楊佳嫻:大家好,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楊佳嫻。歡迎參加「夏日耳朵閱讀節」的第一場活動。今天的主題是性別,活動非常特別,因為我們是三地連線,除了我個人在台北之外,還有在花蓮的程廷Apyang,以及在東京的李琴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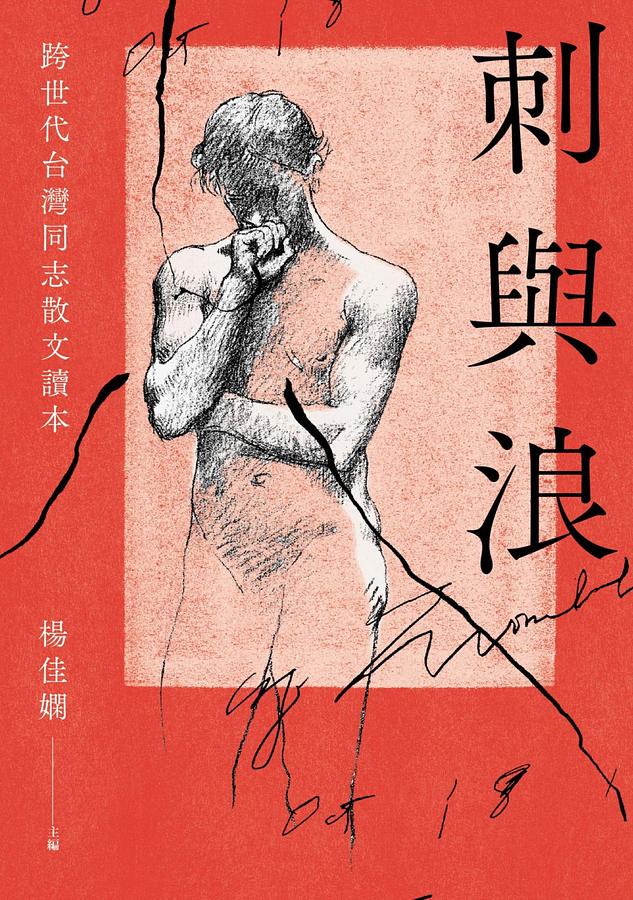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們三位。我自己過去比較讓大家熟悉的身分是創作者,我同時也在大學教書。我會出現在跟性別有關的場合,一方面是因為我最近編了一本跨世代的台灣同志散文選,《刺與浪》;另一方面,我也參與好幾年的性別運動,雖然不是街頭的衝組,但是我擔任台灣的性別運動組織「伴侶盟」的常務理事,非常關心這方面的議題。我是研究文學的,對於同志文學、同志書寫也特別感興趣,今天非常榮幸可以跟兩位寫作者進行跟性別有關的對談。
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們三位。我自己過去比較讓大家熟悉的身分是創作者,我同時也在大學教書。我會出現在跟性別有關的場合,一方面是因為我最近編了一本跨世代的台灣同志散文選,《刺與浪》;另一方面,我也參與好幾年的性別運動,雖然不是街頭的衝組,但是我擔任台灣的性別運動組織「伴侶盟」的常務理事,非常關心這方面的議題。我是研究文學的,對於同志文學、同志書寫也特別感興趣,今天非常榮幸可以跟兩位寫作者進行跟性別有關的對談。
今天來賓之一的李琴峰,是來自台灣的中日雙語的寫作者、翻譯者。她從2013年開始住在日本,在日本已經獲得好幾個文學獎,相信關心文學的朋友都非常清楚。其中幾本作品目前在台灣都已經出版,比如各位可以在鏡好聽聽到朗讀版本的《獨舞》,以及《倒數五秒月牙》、《北極星灑落之夜》、《彼岸花盛開之島》。因為琴峰精通中日兩種語言,她也翻譯了東山彰良的作品,還有可能現場很多人都讀過的,李屏瑤的《向光植物》。
另外一位來賓程廷Apyang,他是太魯閣族人,現在住在花蓮支亞干部落,畢業於台大城鄉所。大家如果查博客來的作者簡介,其實非常有趣,因為他參與非常多社區發展和部落事務。我看到Apyang的個人簡介,非常想問「部落簡易自來水委員會總幹事」這個職位通常是做什麼事情?他目前出版了一本散文集,叫做《我長在打開的樹洞》,寫到部落跟性別方面的經驗,寫得非常有趣,又打開我們對於這些議題的想像視野。
李琴峰:大家好,我是李琴峰,我現在住在東京。因為疫情的關係以及種種因素,沒有辦法到台灣跟大家見面。我的視訊背景是虛擬背景,這是2016年我到雪梨參加同志驕傲活動拍的照片,剛好因為6月是全球同志驕傲月,所以就放這個背景,請大家多多指教。
楊佳嫻:謝謝琴峰。相信如果線上朋友有讀過《獨舞》的話,應該也會記得裡面有雪梨的相關段落。
➤部落簡易自來水委員會總幹事,到底要做些什麼?
Apyang:大家好,我的名字叫Apyang,我現在住在花蓮萬榮鄉的支亞干部落,很高興可以參與這個活動,希望大家有什麼問題都可以盡量提出來。
楊佳嫻:可以問一下「部落簡易自來水委員會總幹事」這個工作的內容嗎?我覺得超酷的。
Apyang:因為我們部落裡面,很多地方是在山區嘛,一般的自來水公司不會牽水上去,不會幫我們處理水的問題。所以我們部落有管理水的委員會,每3年都要選一次主任委員等等。剛回來部落的時候,大家想說你會打電腦,就去當總幹事了,就是處理行政、公文、做紀錄、做報表等等。
楊佳嫻:我覺得這個經驗還滿有意思的,很少看到文學創作者的簡歷上面,會出現這樣的工作。
今天的對談,首先希望把重點放在兩位創作的語言、文字的面向。因為琴峰的母語其實是中文,但是她在日本主要是用日語來創作。如果看過Apyang的書,會知道他是漢語跟族語交互使用。
 琴峰,我們知道你第一部出版的《獨舞》原來是用日文寫作。你曾經創作過中文的作品嗎?在什麼契機下,你決定要用另外一種語言來寫作?我覺得滿有趣的是,為什麼一開始就想用外語寫作、進入外語的文壇,而不是母語的文壇?在文學創作的使用上,中文與日文兩者的語感有沒有關鍵性的差異?
琴峰,我們知道你第一部出版的《獨舞》原來是用日文寫作。你曾經創作過中文的作品嗎?在什麼契機下,你決定要用另外一種語言來寫作?我覺得滿有趣的是,為什麼一開始就想用外語寫作、進入外語的文壇,而不是母語的文壇?在文學創作的使用上,中文與日文兩者的語感有沒有關鍵性的差異?
➤用日文書寫,起因竟是投稿回台灣郵資太貴?!
李琴峰:我大概從國二的時候開始嘗試寫作,寫一些可能不怎麼像樣的小說、散文。那時候當然還不會日文,英文也寫不出來,所以也只能用自己的母語,也就是中文寫。所以在我創作的習作過程,基本上都是用中文,主要都是寫短篇小說、短篇散文。
在台灣也沒寫出什麼太了不起的成績。後來因為唸研究所到日本來,當時我的日文已經有一定的程度,研究所念的是日語教育,已經不是學日文,而是學如何教日文。再加上生活周遭都是日文,去上課、寫報告、寫論文,全部都是用日文。我在日本看到很多來自台灣的留學生,大家都喜歡聚在一起,我比較不會這樣,我會盡量融入日本的社會,可能參加當地的活動,然後認識日本朋友。國籍對我來講不是太大的隔閡,自然融入當地生活,生活裡面很自然地都是日文。
閱讀的部分,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,2011年日幣真的漲得非常貴,在台灣要買日文書非常不容易,非常貴。我是窮學生,買不起。到日本之後,就比較能夠拿到日文書來閱讀,比如日文小說等等。漸漸累積閱讀的經歷之後,對日文小說的寫法或者說腔調,漸漸有一些掌握。即使如此,我還是不覺得自己有辦法用日文寫作。在念研究所階段,雖然我會用日文寫論文、寫報告,但是要寫小說還是太困難了。
到底為什麼會開始用日文寫?其實真的是偶然。比較現實的問題是,假如我在日本,然後還用中文去寫、投稿台灣的文學獎,這樣郵資太貴了。
開始用日文寫真的是偶然。2016年我開始在日本的公司上班,當一個上班族。那時候是4月,日本開學的時候,也是櫻花盛開的季節。某天早上,我在前往公司的電車裡面,那是所謂的滿員電車,人很擠的那一種,我看到外面櫻花開得非常漂亮,然後自己搭乘滿員電車,就想說,我以後都要這樣過生活嗎?不知道為什麼,突然一個單詞浮現出來,就是「死ぬ」,這是日文的死亡。
記得我大概從青春期吧,10幾歲的時候,一直有種淡淡的,日文叫「希死念慮」(きしねんりょ),中文叫「自殺願望」之類的,覺得好像活著也沒什麼意義。我心中一直都有一種關於死亡的念頭,剛好就在2016年4月那個時間點,用日文的形式,從心裡浮現出來。
學過日文的朋友可能會知道,「死ぬ」是一個動詞,是滿特殊的動詞,在現代日文的所有動詞裡,只有這個詞是以ぬ結尾,其實這是滿意外的一個巧合。那天就不斷地胡思亂想,想說這個好像可以變成一篇小說的開頭,因為一開始這個詞彙是用日文的形式浮現,我就想說不如用日文寫,寫出來了就是《獨舞》。因為第一篇就是用日文寫的,拿去投日本的文學獎,很幸運得了一個小獎,然後就出道,之後滿自然就一直用日文寫。
➤Kari,太魯閣族語「聊天」,有時候也可以翻「咖哩」(才不是
楊佳嫻:謝謝琴峰的分享。確實大家如果手邊有《獨舞》的話,可以翻開第一頁,第一個字就是「死」。
用外語寫作的作家,比如哈金,他講過,因為他在美國用英語寫作,這不是他最熟悉的語言,因此他會傾向用更簡明、簡潔的句式來寫,反而會造成一種比較特殊的、不一樣的文體。這部分也許等一下還有時間的話,琴峰也可以再稍微回應一下。
我們先請Apyang來談一談,學習族語對於你在文學創作的幫助是什麼?加入族語,跟全部都用漢語或中文來寫,有什麼不同的效果跟意義?
Apyang:我會在創作裡面加入族語,其實有幾個想法。以前我在唸原住民前輩的文學作品的時候,當時羅馬拼音還沒有那麼盛行,他們一定得把族語翻成漢字,讓一般人去閱讀。可是有些族語翻成漢字真的很奇怪,變成我在創作上的一個困擾。比方說我的名字Apyang,翻成中文就滿奇怪的。
再來,其實族語翻譯在文學上有很多彈性,因為我不是在編太魯閣族語字典,在兩個語言上的轉換,有很多我覺得很好玩的文字遊戲。比方我的作品裡面有講,田裡的工寮叫做Biyi,我就直接翻譯成「彼憶」。或者我們講勞動或田裡的工作叫Qmpah,我覺得它有滿可以對應的字,我用漢字的「耕」,剛好有一起去工作的那種感覺。然後我們有個話叫Kari,是語言、聊天的意思。我有篇散文是在講養雞的時候,我跟雞寮裡火雞的故事。因為很多聊天的情境是在吃東西的時候,我直接把它翻譯成中文的「咖哩」,會變得非常有趣。
有些字如果硬翻,或是把它音譯成漢字,是滿詭異的事情。再加上剛剛講的,因為我自己是創作者,具有把兩種語言進行轉換的空間,我自己在玩文字的時候也覺得很有意思,可以傳達我的一些想法,有些純粹是我覺得文字上很好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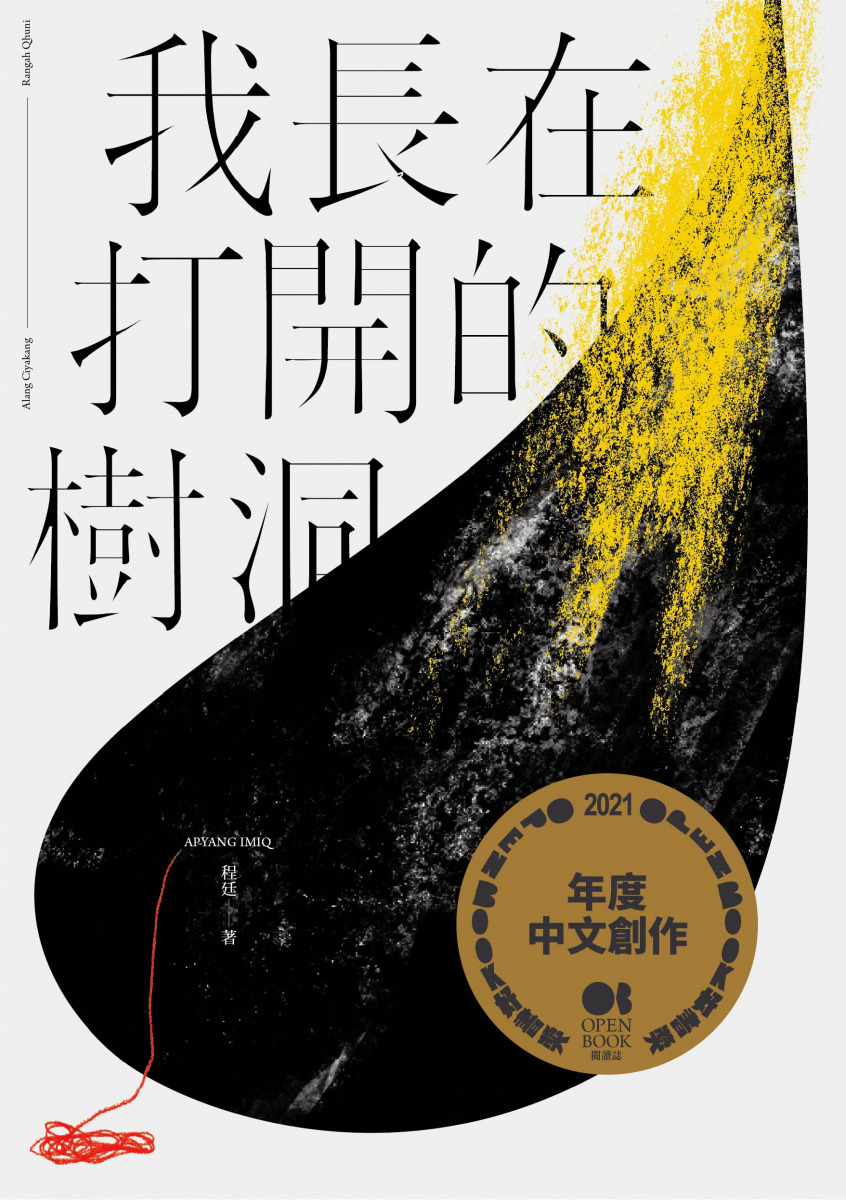 《我長在打開的樹洞》是我的第一篇創作集。其實現在部落裡,不見得大家會全族語或者全漢語溝通。很多老人家可能族語講得不錯,但華語講得不像年輕人這麼好,所以跟我們講話的時候都會穿插族語。語言穿插的情況是我們很日常的狀態,我在散文裡滿想要呈現支亞干部落的日常對話情境,所以會有很多族語穿插在漢字裡面。雖然整體來講,這本書還是以華語為主的創作,但我很希望可以呈現太魯閣語在裡面。
《我長在打開的樹洞》是我的第一篇創作集。其實現在部落裡,不見得大家會全族語或者全漢語溝通。很多老人家可能族語講得不錯,但華語講得不像年輕人這麼好,所以跟我們講話的時候都會穿插族語。語言穿插的情況是我們很日常的狀態,我在散文裡滿想要呈現支亞干部落的日常對話情境,所以會有很多族語穿插在漢字裡面。雖然整體來講,這本書還是以華語為主的創作,但我很希望可以呈現太魯閣語在裡面。
➤發明新族語描繪現代事物?
楊佳嫻:謝謝Apyang的分享。確實,我們讀這個作品,可以發現創作者雖然有意把一些族語單詞跟華語混雜,但同時又做了一些帶有詩意的翻譯。它其實是太魯閣族人的日常,平常講話就這樣。
這讓我進一步好奇,在太魯閣族語裡面,對於現代的事物並不會發明新的詞去描述,而是直接用華語來講嗎?
Apyang:對,有滿多情況會是這樣,或者是用日語。
楊佳嫻、李琴峰:有什麼例子嗎?
Apyang:比如電影。有時候也會借用閩南語。
楊佳嫻:所以現在在你們族裡,年紀很大的老人家可能還是會講點日文?
Apyang:會喔,他們日語很好。
楊佳嫻:我覺得很有趣。我想到1961年張愛玲來過一次台灣,她覺得台北很無聊,一直要去花蓮。她留下來的遊記裡面說,她遇到的原住民(當然她不是用原住民這個詞,她當時會用「山地」這個詞),全部都是講日文,日文好得驚人,顯然對她而言是很驚訝的事情。
我們再回到琴峰,因為你自己是外國人寫日文,你也會採取某一些語言策略,甚至產生跟其他日語作家不太一樣的文體嗎?
➤表音文字的強大與表意文字的黏稠
李琴峰:老實說,關於文體,每個作家都各有不同,所以我也不大能夠說,我跟所謂以日文為母語的作家不同。我覺得每個人都不同,所以也沒必要特別去區分你的母語是不是日文。
不過想提的是,中文跟日文是完全不一樣的語言,在語言學上的分類也不一樣。雖然可能有千年以上的交流,但真的完全不一樣。當我學會日文並開始以日文創作之後,我感受很深的是,表音文字真是太強大了。漢字雖然有些是形聲字,有表達聲音的一些要素,但基本上還是表意文字。表意文字在書寫上有它的效果,但同時也有侷限,比方說有些你想傳達的聲音,就是沒有字可以表現,這些中文就寫不出來。
日文也用漢字,但是日文同時又有假名(平假名、片假名),是表音文字,當你想寫出某些效果、表達某些聲音,就可以用表音文字表達。又或者,在寫對白的時候,每個人講話的方式基本上是不一樣的,每個人的腔調也是不一樣的。有些人可能發音比較好,有些可能聲音拉得比較長,有些人可能講話比較快之類的,這樣的對話腔調的不同,有時候很難單用表意文字去表達。在這個面向上,其實日文的表達功能是滿強大的。
像剛剛Apyang說,有些族語不知道怎麼用中文的漢字去表達,我覺得是有共通的,你怎麼寫都覺得很卡。因為中文的漢字是每個字都有份量,不像日文的假名,一個字就是一個音,也沒有特定的意思,感覺就比較輕巧。
 當然中文的漢字也有它的好處。因為每個漢字都有意思,都有重量,所以可以創造出其他語言表現不出來的效果,比方說一種黏稠性,或者是一種文字的密度。我覺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《荒人手記》,文體真的非常稠密。《荒人手記》有日文版,對照之後會發現文字多了一倍。中文的密度非常高,把它翻譯成日文,密度必然會被稀釋。因為日文必須要有假名,不能全部都用漢字,日文就比較難寫出這樣高密度的文體。
當然中文的漢字也有它的好處。因為每個漢字都有意思,都有重量,所以可以創造出其他語言表現不出來的效果,比方說一種黏稠性,或者是一種文字的密度。我覺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《荒人手記》,文體真的非常稠密。《荒人手記》有日文版,對照之後會發現文字多了一倍。中文的密度非常高,把它翻譯成日文,密度必然會被稀釋。因為日文必須要有假名,不能全部都用漢字,日文就比較難寫出這樣高密度的文體。
楊佳嫻:謝謝。這個牽涉滿廣的,比如說有一些情緒或聲音,怎樣簡單而傳神的表達?或者有些新的詞彙,怎樣在自己的語言把它寫定?這其實好像都得經過一定程度的時間與過程。
我剛剛立刻想到的是,大約100年前,當時有個詩人,就是大家熟悉的胡適,他想寫我們今天叫做「野餐」、Picnic的詞,但這個詞的翻譯當時還沒有固定,詩人不知道該怎麼寫,最後只好音譯,而且把它放在七言的長詩,放在古詩體裡面,寫成「辟克匿克來江邊」。一開始看,根本不知「辟克匿克」是什麼,你要唸出聲音,才可能聯想到是英文的那個詞。我們在100年後來讀,會有一種特殊的趣味。●
Tags:
楊佳嫻:大家好,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楊佳嫻。歡迎參加「夏日耳朵閱讀節」的第一場活動。今天的主題是性別,活動非常特別,因為我們是三地連線,除了我個人在台北之外,還有在花蓮的程廷Apyang,以及在東京的李琴峰。
今天來賓之一的李琴峰,是來自台灣的中日雙語的寫作者、翻譯者。她從2013年開始住在日本,在日本已經獲得好幾個文學獎,相信關心文學的朋友都非常清楚。其中幾本作品目前在台灣都已經出版,比如各位可以在鏡好聽聽到朗讀版本的《獨舞》,以及《倒數五秒月牙》、《北極星灑落之夜》、《彼岸花盛開之島》。因為琴峰精通中日兩種語言,她也翻譯了東山彰良的作品,還有可能現場很多人都讀過的,李屏瑤的《向光植物》。
另外一位來賓程廷Apyang,他是太魯閣族人,現在住在花蓮支亞干部落,畢業於台大城鄉所。大家如果查博客來的作者簡介,其實非常有趣,因為他參與非常多社區發展和部落事務。我看到Apyang的個人簡介,非常想問「部落簡易自來水委員會總幹事」這個職位通常是做什麼事情?他目前出版了一本散文集,叫做《我長在打開的樹洞》,寫到部落跟性別方面的經驗,寫得非常有趣,又打開我們對於這些議題的想像視野。
李琴峰:大家好,我是李琴峰,我現在住在東京。因為疫情的關係以及種種因素,沒有辦法到台灣跟大家見面。我的視訊背景是虛擬背景,這是2016年我到雪梨參加同志驕傲活動拍的照片,剛好因為6月是全球同志驕傲月,所以就放這個背景,請大家多多指教。
楊佳嫻:謝謝琴峰。相信如果線上朋友有讀過《獨舞》的話,應該也會記得裡面有雪梨的相關段落。
➤部落簡易自來水委員會總幹事,到底要做些什麼?
Apyang:大家好,我的名字叫Apyang,我現在住在花蓮萬榮鄉的支亞干部落,很高興可以參與這個活動,希望大家有什麼問題都可以盡量提出來。
楊佳嫻:可以問一下「部落簡易自來水委員會總幹事」這個工作的內容嗎?我覺得超酷的。
Apyang:因為我們部落裡面,很多地方是在山區嘛,一般的自來水公司不會牽水上去,不會幫我們處理水的問題。所以我們部落有管理水的委員會,每3年都要選一次主任委員等等。剛回來部落的時候,大家想說你會打電腦,就去當總幹事了,就是處理行政、公文、做紀錄、做報表等等。
楊佳嫻:我覺得這個經驗還滿有意思的,很少看到文學創作者的簡歷上面,會出現這樣的工作。
今天的對談,首先希望把重點放在兩位創作的語言、文字的面向。因為琴峰的母語其實是中文,但是她在日本主要是用日語來創作。如果看過Apyang的書,會知道他是漢語跟族語交互使用。
➤用日文書寫,起因竟是投稿回台灣郵資太貴?!
李琴峰:我大概從國二的時候開始嘗試寫作,寫一些可能不怎麼像樣的小說、散文。那時候當然還不會日文,英文也寫不出來,所以也只能用自己的母語,也就是中文寫。所以在我創作的習作過程,基本上都是用中文,主要都是寫短篇小說、短篇散文。
在台灣也沒寫出什麼太了不起的成績。後來因為唸研究所到日本來,當時我的日文已經有一定的程度,研究所念的是日語教育,已經不是學日文,而是學如何教日文。再加上生活周遭都是日文,去上課、寫報告、寫論文,全部都是用日文。我在日本看到很多來自台灣的留學生,大家都喜歡聚在一起,我比較不會這樣,我會盡量融入日本的社會,可能參加當地的活動,然後認識日本朋友。國籍對我來講不是太大的隔閡,自然融入當地生活,生活裡面很自然地都是日文。
閱讀的部分,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,2011年日幣真的漲得非常貴,在台灣要買日文書非常不容易,非常貴。我是窮學生,買不起。到日本之後,就比較能夠拿到日文書來閱讀,比如日文小說等等。漸漸累積閱讀的經歷之後,對日文小說的寫法或者說腔調,漸漸有一些掌握。即使如此,我還是不覺得自己有辦法用日文寫作。在念研究所階段,雖然我會用日文寫論文、寫報告,但是要寫小說還是太困難了。
到底為什麼會開始用日文寫?其實真的是偶然。比較現實的問題是,假如我在日本,然後還用中文去寫、投稿台灣的文學獎,這樣郵資太貴了。
開始用日文寫真的是偶然。2016年我開始在日本的公司上班,當一個上班族。那時候是4月,日本開學的時候,也是櫻花盛開的季節。某天早上,我在前往公司的電車裡面,那是所謂的滿員電車,人很擠的那一種,我看到外面櫻花開得非常漂亮,然後自己搭乘滿員電車,就想說,我以後都要這樣過生活嗎?不知道為什麼,突然一個單詞浮現出來,就是「死ぬ」,這是日文的死亡。
記得我大概從青春期吧,10幾歲的時候,一直有種淡淡的,日文叫「希死念慮」(きしねんりょ),中文叫「自殺願望」之類的,覺得好像活著也沒什麼意義。我心中一直都有一種關於死亡的念頭,剛好就在2016年4月那個時間點,用日文的形式,從心裡浮現出來。
學過日文的朋友可能會知道,「死ぬ」是一個動詞,是滿特殊的動詞,在現代日文的所有動詞裡,只有這個詞是以ぬ結尾,其實這是滿意外的一個巧合。那天就不斷地胡思亂想,想說這個好像可以變成一篇小說的開頭,因為一開始這個詞彙是用日文的形式浮現,我就想說不如用日文寫,寫出來了就是《獨舞》。因為第一篇就是用日文寫的,拿去投日本的文學獎,很幸運得了一個小獎,然後就出道,之後滿自然就一直用日文寫。
➤Kari,太魯閣族語「聊天」,有時候也可以翻「咖哩」(才不是
楊佳嫻:謝謝琴峰的分享。確實大家如果手邊有《獨舞》的話,可以翻開第一頁,第一個字就是「死」。
用外語寫作的作家,比如哈金,他講過,因為他在美國用英語寫作,這不是他最熟悉的語言,因此他會傾向用更簡明、簡潔的句式來寫,反而會造成一種比較特殊的、不一樣的文體。這部分也許等一下還有時間的話,琴峰也可以再稍微回應一下。
我們先請Apyang來談一談,學習族語對於你在文學創作的幫助是什麼?加入族語,跟全部都用漢語或中文來寫,有什麼不同的效果跟意義?
Apyang:我會在創作裡面加入族語,其實有幾個想法。以前我在唸原住民前輩的文學作品的時候,當時羅馬拼音還沒有那麼盛行,他們一定得把族語翻成漢字,讓一般人去閱讀。可是有些族語翻成漢字真的很奇怪,變成我在創作上的一個困擾。比方說我的名字Apyang,翻成中文就滿奇怪的。
再來,其實族語翻譯在文學上有很多彈性,因為我不是在編太魯閣族語字典,在兩個語言上的轉換,有很多我覺得很好玩的文字遊戲。比方我的作品裡面有講,田裡的工寮叫做Biyi,我就直接翻譯成「彼憶」。或者我們講勞動或田裡的工作叫Qmpah,我覺得它有滿可以對應的字,我用漢字的「耕」,剛好有一起去工作的那種感覺。然後我們有個話叫Kari,是語言、聊天的意思。我有篇散文是在講養雞的時候,我跟雞寮裡火雞的故事。因為很多聊天的情境是在吃東西的時候,我直接把它翻譯成中文的「咖哩」,會變得非常有趣。
有些字如果硬翻,或是把它音譯成漢字,是滿詭異的事情。再加上剛剛講的,因為我自己是創作者,具有把兩種語言進行轉換的空間,我自己在玩文字的時候也覺得很有意思,可以傳達我的一些想法,有些純粹是我覺得文字上很好玩。
➤發明新族語描繪現代事物?
楊佳嫻:謝謝Apyang的分享。確實,我們讀這個作品,可以發現創作者雖然有意把一些族語單詞跟華語混雜,但同時又做了一些帶有詩意的翻譯。它其實是太魯閣族人的日常,平常講話就這樣。
這讓我進一步好奇,在太魯閣族語裡面,對於現代的事物並不會發明新的詞去描述,而是直接用華語來講嗎?
Apyang:對,有滿多情況會是這樣,或者是用日語。
楊佳嫻、李琴峰:有什麼例子嗎?
Apyang:比如電影。有時候也會借用閩南語。
楊佳嫻:所以現在在你們族裡,年紀很大的老人家可能還是會講點日文?
Apyang:會喔,他們日語很好。
楊佳嫻:我覺得很有趣。我想到1961年張愛玲來過一次台灣,她覺得台北很無聊,一直要去花蓮。她留下來的遊記裡面說,她遇到的原住民(當然她不是用原住民這個詞,她當時會用「山地」這個詞),全部都是講日文,日文好得驚人,顯然對她而言是很驚訝的事情。
我們再回到琴峰,因為你自己是外國人寫日文,你也會採取某一些語言策略,甚至產生跟其他日語作家不太一樣的文體嗎?
➤表音文字的強大與表意文字的黏稠
李琴峰:老實說,關於文體,每個作家都各有不同,所以我也不大能夠說,我跟所謂以日文為母語的作家不同。我覺得每個人都不同,所以也沒必要特別去區分你的母語是不是日文。
不過想提的是,中文跟日文是完全不一樣的語言,在語言學上的分類也不一樣。雖然可能有千年以上的交流,但真的完全不一樣。當我學會日文並開始以日文創作之後,我感受很深的是,表音文字真是太強大了。漢字雖然有些是形聲字,有表達聲音的一些要素,但基本上還是表意文字。表意文字在書寫上有它的效果,但同時也有侷限,比方說有些你想傳達的聲音,就是沒有字可以表現,這些中文就寫不出來。
日文也用漢字,但是日文同時又有假名(平假名、片假名),是表音文字,當你想寫出某些效果、表達某些聲音,就可以用表音文字表達。又或者,在寫對白的時候,每個人講話的方式基本上是不一樣的,每個人的腔調也是不一樣的。有些人可能發音比較好,有些可能聲音拉得比較長,有些人可能講話比較快之類的,這樣的對話腔調的不同,有時候很難單用表意文字去表達。在這個面向上,其實日文的表達功能是滿強大的。
像剛剛Apyang說,有些族語不知道怎麼用中文的漢字去表達,我覺得是有共通的,你怎麼寫都覺得很卡。因為中文的漢字是每個字都有份量,不像日文的假名,一個字就是一個音,也沒有特定的意思,感覺就比較輕巧。
楊佳嫻:謝謝。這個牽涉滿廣的,比如說有一些情緒或聲音,怎樣簡單而傳神的表達?或者有些新的詞彙,怎樣在自己的語言把它寫定?這其實好像都得經過一定程度的時間與過程。
我剛剛立刻想到的是,大約100年前,當時有個詩人,就是大家熟悉的胡適,他想寫我們今天叫做「野餐」、Picnic的詞,但這個詞的翻譯當時還沒有固定,詩人不知道該怎麼寫,最後只好音譯,而且把它放在七言的長詩,放在古詩體裡面,寫成「辟克匿克來江邊」。一開始看,根本不知「辟克匿克」是什麼,你要唸出聲音,才可能聯想到是英文的那個詞。我們在100年後來讀,會有一種特殊的趣味。●
手指點一下,您支持的每一分錢
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
➤以文學為認同發聲,完整側記
【Openbook國際書展參戰(;・`д・´)】
2/6(五)歡迎加入玩耍!•̀.̫•́✧書寫、行動與反思:和島嶼互動的幾種方式
閱讀通信 vol.367》如果我在晚上九點敲響你的房門
延伸閱讀
以文學為認同發聲II》多重弱勢中,摸索賴以為生的奇蹟ft. 楊佳嫻、李琴峰、Apyang Imiq(程廷)
「鏡好聽夏日耳朵閱讀節」首場活動「以文學為認同發聲:當代性別書寫——台北、花蓮、東京,全球同志驕傲月跨境連線」邀請到了學者楊佳嫻、作家李琴峰、Apyang Imiq(程廷),... 閱讀更多
以文學為認同發聲III》創造更理想的社會共同體 ft.楊佳嫻、李琴峰、Apyang Imiq(程廷)
「鏡好聽夏日耳朵閱讀節」首場活動「以文學為認同發聲:當代性別書寫——台北、花蓮、東京,全球同志驕傲月跨境連線」邀請到了學者楊佳嫻、作家李琴峰、Apyang Imiq(程廷),... 閱讀更多
閱讀隨身聽S5EP10》作家李琴峰+聯合文學總編周昭翡/認識世界的寬廣,能成為生存意志的來源
你那邊,現在是白天還是晚上?已回到家,或是在通勤的路上?無論什麼時間、地點,歡迎隨時打開「閱讀隨身聽」。Openbook閱讀誌企畫製作的Podcast節目,... 閱讀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