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與友人經常玩的一個遊戲,是為自己不滿意的作品設想一些可能的修訂。例如談起《坂道上的阿波羅》,「如果結尾的時候千太郎真的死掉的話,就會變得很厲害吶。」
「或者重逢的時候,兩個人的演奏技術都變很差,那樣也很惆悵,很棒。」
玩這個遊戲的時候,我與我的友人是殘酷的。「都當醫生當了7、8年,手指怎麼可能還那麼了解鋼琴呢?」角色的生命,作者的仁慈,以及世上幾千幾萬雙和我們共享那個故事的眼睛,忽然被我們放在次要的位置。一切以「創作」為優先,以「這樣寫比較好」為優先——我與我的友人知道,這樣的情境只能是遊戲,因為真正重要的事情往往是反戲劇性的。生活並不以精彩為最高原則來發生,我們只是比較喜歡那樣而已。
帥氣,戲劇性,伴隨英雄敘事的個人主義,還有情節大於意義的悲壯之舉。後來我們都知道了,活下來的人註定無法成為格瓦拉,因為那是格瓦拉的定義本身。然而,每個人的生命中,都確實有過把澎湃慷慨的東西,擺在重要卻無聊的事情之前的時刻。對我來說,這樣的例外狀態就是所謂的青春。
而「老去」,對我來說就是這份優先順位改變的過程:當我們終於把重要的事情,放在名副其實重要的順序上。當我們下樓梯時不再一次跨個三四個臺階,因為那樣會跌倒(但小時候那樣下樓梯,難道是因為小時候不會跌倒嗎?)當我們不再寫歌了,因為沒有人聽——在這層意義上,我一直認為,創作者就是把生命中的這種例外狀態無限延長下去的人。
某些時候,當一個作品真的穿過我們的生命的時候,我們也會暫時回到那個例外狀態,想起那些,不重要的事情對我們非常重要的時期。
在我的生命中,熊就是這樣一個,能夠延長他人的例外狀態的人。
有趣的是,《臺北是我的夢幻島》卻反而不是這種狀態的作品。
相反地,它所書寫的正是熊自己的例外狀態的末端、那個(或說這個?)內在的優先順位一一移轉、歸位的時期,那些讓我與我的友人以及像我們一樣的人完成我們的老去的事件,模糊忽然清澈的瞬間,還有當我們還不知道原來模糊保護著、率領著我們的時候,所發生的事。
一部見證自己例外狀態的終結的作品。寫起來一定非常痛吧。如果結尾的時候千太郎真的死掉的話,的那種痛。
我們可以直接把臺北比擬為文學嗎?
這個比法,在各種層面上都極不正確,對我來說卻是一把清晰透視《臺北是我的夢幻島》的鑰匙。當我們把同名散文中的每一個「臺北」都替換成「文學」,其中的拉鋸和抒情都有了另一層意思:
「說真的,有哪個臺灣人不喜歡看人談論臺北文學,說臺北文學壞話?臺北文學人或許是,但他們會假裝喜歡,附和其他人說的壞話,然後在心裡想:還是我嫌棄得更到位。」
「真正進入臺北文學時,我並沒有特別的想法。那不是一個選擇,而是自然現象。」
「臺北文學最令我難以割捨的是,這裡有無限多個討厭臺北文學的理由,只有臺北文學才找得到這麼多。我可以在剛睡醒時喜歡它,在穿衣時厭惡它,在移動時享受,在吃飯時沮喪,在睡前的狂歡重新愛上,我每天都能分裂成5個,去體驗豐富5倍的刺激,就算遇到難受的事,也只受了五分之一的傷。」
「當他看著臺北文學,他就暫時消失了。」
不知道有意或無意,熊在書寫時,將文學和臺北在場域、個人經驗等意義上疊合在一起。例如當他寫自己踏入寫作的內心活動:
「我覺得,我是有寫作才能的。⋯⋯沒有作家、沒有文學,只有寫,寫作文、寫作故事。回頭想想,我就是喜歡這件事。」(那不是一個選擇,而是自然現象。)
例如,寫對文學介入現實的矛盾與浪漫:
「324過後,一群死文青組成的輕痰讀書會向我們認識的許多寫作者邀稿,印了兩份《街頭副刊》在靜坐現場發送,嚷嚷『有人需要文學嗎』。我自己並不非常清楚這樣做有什麼意義,也沒有餘力思考。我認真希望拯救過自己的文學能夠拯救其他人,但這種心態不就跟為壓根不信教的人祈禱一樣嗎?我可以列出一百個不應該這麼做的理由,但沒有一個成功阻止我。」(這裡有無限多個討厭它的理由。)
又例如寫「寫作」與自身的關係:
「追尋自我價值的寫作,多少也是渴望報復他人的寫作。若對表現溫柔有所執著,多少也由於看清自身行使的暴力。若是一直寫下去,還得為那麼多沒能在寫的人寫作,替他們指認事物。只有將正反兩面全部攤開,我才能說服自己,算是滿足了能夠寫作的最低標準。」(當他看著它,他就暫時消失了。)
而籠罩著這些文學情結的巨大背景,反過來又可以用北上遊子的臺北情結去詮釋,並且投射到熊對性別、對親密關係、對次文化場景的思考上:當他質問自己有沒有資格寫作、有沒有資格當一個伴侶、有沒有資格當一個異男、夠不夠「酷」,往往從自己「本來不是」的立場出發,一種自視為外來者的姿態。
非臺北人想要成為臺北人的生長痛。最可怕的是,如果失敗了,這個背景又總讓我們覺得是自己的錯。這是臺北的黑魔法,臺北的文學性,讓我們忘了去問:難道生長是可以失敗的嗎?
一定非常痛吧。懷疑自己到底能不能長大的那種痛。
於是,當書中的熊終於不再把「文學」的終極理型視為自我的完成,那本應是青春的消逝的悵然,卻同時有了更幽微、更積極的意義——放下。不同於放棄,放下是讓一件事情不再審視自己,是肯認自己「已經是」什麼。
這部作品藉此提醒了讀者,浪漫的例外狀態的末端,並不等於一切的結束。它只是某段時期的尾聲而已,而非所有事情的結局。
而我與熊經常玩的一個遊戲,是把自己的作品丟給對方看,要對方假裝不滿意它。然後,設想一些可能的修訂。
我也是這樣第一次讀到這部書稿的。當時我這樣回訊:
「在書裡,台北就是文學。而整本書有一個潛流,是離開台北,也就是放下文學。令我感到最迷人之處,是你成功把『寫作』和『文學』切分開來,自然到彷彿把『唱歌』和『音樂』切分開來一樣。光是這一點,這部作品已經贏了。」
「在書中,與『文學』拉鋸的,是『生活和愛情』。放在全書的脈絡下看,〈少年經事〉原來不只是在談性別,而是在談生活對創作的那道反作用力啊。(好好笑,我太慢了嗎,之前根本沒讀懂嗎)。在這個理解之下,我會建議〈預告〉和〈寫作〉的篇序一起提前到〈可是亂馬就可以〉之後,讓『離開台北/放下文學』的領悟,提前到全書大概第二幕下的位置⋯⋯」
「我好想直接稱呼這本書為《反文青》(?)」我最後寫,「我有資格提這件事嗎?總之我還是提了。拉票的理由:A. 這本書的修辭意圖低,取這個書名可以給那些不懂這樣有多好的人預先的直擊。B. 直接陳述本書主軸,而不經過象徵或典故,我覺得是近來讀者的偏好趨勢。C. 具有一丁點引戰的話題性,但不至於炎上。D. 氣勢上如同少年漫畫的絕招般帥氣。」
熊讀了我長長的訊息,然後回:「給我一點時間消化一下。」
這本書終究沒有改名為《反文青》。我喜歡這個一點也不戲劇性的結局。●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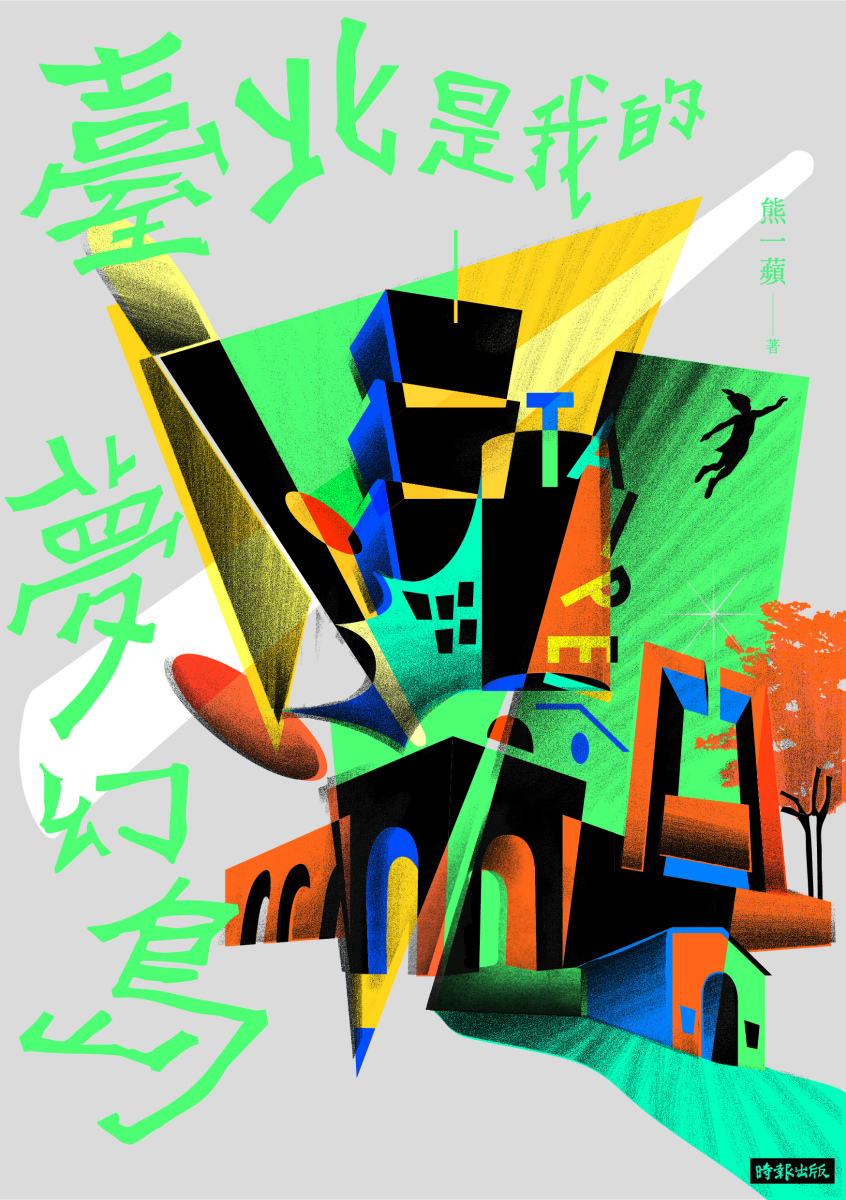 臺北是我的夢幻島 臺北是我的夢幻島
作者:熊一蘋
出版:時報出版
定價:380元
【內容簡介➤】
|
|
作者簡介:熊一蘋
本名熊信淵,高雄鳳山人,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。大學和畢業後幾年長期為臺北居民,2022年決定搬回南部。曾獲林榮三文學獎、聯合報文學獎等。作品主題以文學、獨立音樂、戰後大眾史為主。曾出版非虛構作品《我們的搖滾樂》、《華美的跫音:1960年代美軍文化影響下的臺中生活》。
|
Tags:
本文標題「乒乓」出自日本漫畫家松本大洋於1996至97年連載的短篇運動漫畫,描寫兩名高中乒乓球選手從童年玩伴到成為競技對手的過程。作品筆觸粗獷、構圖具動態感,著重角色心理描寫與個人內在動機的探索。雖以運動為題,主軸更聚焦於成長、自我認同與勝負之外的價值。(底圖來源:unsplash)
我與友人經常玩的一個遊戲,是為自己不滿意的作品設想一些可能的修訂。例如談起《坂道上的阿波羅》,「如果結尾的時候千太郎真的死掉的話,就會變得很厲害吶。」
「或者重逢的時候,兩個人的演奏技術都變很差,那樣也很惆悵,很棒。」
玩這個遊戲的時候,我與我的友人是殘酷的。「都當醫生當了7、8年,手指怎麼可能還那麼了解鋼琴呢?」角色的生命,作者的仁慈,以及世上幾千幾萬雙和我們共享那個故事的眼睛,忽然被我們放在次要的位置。一切以「創作」為優先,以「這樣寫比較好」為優先——我與我的友人知道,這樣的情境只能是遊戲,因為真正重要的事情往往是反戲劇性的。生活並不以精彩為最高原則來發生,我們只是比較喜歡那樣而已。
帥氣,戲劇性,伴隨英雄敘事的個人主義,還有情節大於意義的悲壯之舉。後來我們都知道了,活下來的人註定無法成為格瓦拉,因為那是格瓦拉的定義本身。然而,每個人的生命中,都確實有過把澎湃慷慨的東西,擺在重要卻無聊的事情之前的時刻。對我來說,這樣的例外狀態就是所謂的青春。
而「老去」,對我來說就是這份優先順位改變的過程:當我們終於把重要的事情,放在名副其實重要的順序上。當我們下樓梯時不再一次跨個三四個臺階,因為那樣會跌倒(但小時候那樣下樓梯,難道是因為小時候不會跌倒嗎?)當我們不再寫歌了,因為沒有人聽——在這層意義上,我一直認為,創作者就是把生命中的這種例外狀態無限延長下去的人。
某些時候,當一個作品真的穿過我們的生命的時候,我們也會暫時回到那個例外狀態,想起那些,不重要的事情對我們非常重要的時期。
在我的生命中,熊就是這樣一個,能夠延長他人的例外狀態的人。
有趣的是,《臺北是我的夢幻島》卻反而不是這種狀態的作品。
相反地,它所書寫的正是熊自己的例外狀態的末端、那個(或說這個?)內在的優先順位一一移轉、歸位的時期,那些讓我與我的友人以及像我們一樣的人完成我們的老去的事件,模糊忽然清澈的瞬間,還有當我們還不知道原來模糊保護著、率領著我們的時候,所發生的事。
一部見證自己例外狀態的終結的作品。寫起來一定非常痛吧。如果結尾的時候千太郎真的死掉的話,的那種痛。
我們可以直接把臺北比擬為文學嗎?
這個比法,在各種層面上都極不正確,對我來說卻是一把清晰透視《臺北是我的夢幻島》的鑰匙。當我們把同名散文中的每一個「臺北」都替換成「文學」,其中的拉鋸和抒情都有了另一層意思:
不知道有意或無意,熊在書寫時,將文學和臺北在場域、個人經驗等意義上疊合在一起。例如當他寫自己踏入寫作的內心活動:
例如,寫對文學介入現實的矛盾與浪漫:
又例如寫「寫作」與自身的關係:
而籠罩著這些文學情結的巨大背景,反過來又可以用北上遊子的臺北情結去詮釋,並且投射到熊對性別、對親密關係、對次文化場景的思考上:當他質問自己有沒有資格寫作、有沒有資格當一個伴侶、有沒有資格當一個異男、夠不夠「酷」,往往從自己「本來不是」的立場出發,一種自視為外來者的姿態。
非臺北人想要成為臺北人的生長痛。最可怕的是,如果失敗了,這個背景又總讓我們覺得是自己的錯。這是臺北的黑魔法,臺北的文學性,讓我們忘了去問:難道生長是可以失敗的嗎?
一定非常痛吧。懷疑自己到底能不能長大的那種痛。
於是,當書中的熊終於不再把「文學」的終極理型視為自我的完成,那本應是青春的消逝的悵然,卻同時有了更幽微、更積極的意義——放下。不同於放棄,放下是讓一件事情不再審視自己,是肯認自己「已經是」什麼。
這部作品藉此提醒了讀者,浪漫的例外狀態的末端,並不等於一切的結束。它只是某段時期的尾聲而已,而非所有事情的結局。
而我與熊經常玩的一個遊戲,是把自己的作品丟給對方看,要對方假裝不滿意它。然後,設想一些可能的修訂。
我也是這樣第一次讀到這部書稿的。當時我這樣回訊:
「在書裡,台北就是文學。而整本書有一個潛流,是離開台北,也就是放下文學。令我感到最迷人之處,是你成功把『寫作』和『文學』切分開來,自然到彷彿把『唱歌』和『音樂』切分開來一樣。光是這一點,這部作品已經贏了。」
「在書中,與『文學』拉鋸的,是『生活和愛情』。放在全書的脈絡下看,〈少年經事〉原來不只是在談性別,而是在談生活對創作的那道反作用力啊。(好好笑,我太慢了嗎,之前根本沒讀懂嗎)。在這個理解之下,我會建議〈預告〉和〈寫作〉的篇序一起提前到〈可是亂馬就可以〉之後,讓『離開台北/放下文學』的領悟,提前到全書大概第二幕下的位置⋯⋯」
「我好想直接稱呼這本書為《反文青》(?)」我最後寫,「我有資格提這件事嗎?總之我還是提了。拉票的理由:A. 這本書的修辭意圖低,取這個書名可以給那些不懂這樣有多好的人預先的直擊。B. 直接陳述本書主軸,而不經過象徵或典故,我覺得是近來讀者的偏好趨勢。C. 具有一丁點引戰的話題性,但不至於炎上。D. 氣勢上如同少年漫畫的絕招般帥氣。」
熊讀了我長長的訊息,然後回:「給我一點時間消化一下。」
這本書終究沒有改名為《反文青》。我喜歡這個一點也不戲劇性的結局。●
作者:熊一蘋
出版:時報出版
定價:380元
【內容簡介➤】
作者簡介:熊一蘋
本名熊信淵,高雄鳳山人,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。大學和畢業後幾年長期為臺北居民,2022年決定搬回南部。曾獲林榮三文學獎、聯合報文學獎等。作品主題以文學、獨立音樂、戰後大眾史為主。曾出版非虛構作品《我們的搖滾樂》、《華美的跫音:1960年代美軍文化影響下的臺中生活》。
手指點一下,您支持的每一分錢
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
【Openbook國際書展參戰(;・`д・´)】
2/6(五)歡迎加入玩耍!•̀.̫•́✧書寫、行動與反思:和島嶼互動的幾種方式
閱讀通信 vol.367》如果我在晚上九點敲響你的房門
延伸閱讀
書評》「先研究不傷身體」的台灣熱門音樂:威權時代、文藝青年,從而叛逆不太起來的《我們的搖滾樂》
閱讀更多
評論》孫梓評主編九歌110年散文選:為什麼你還需要一本年度散文選?
閱讀更多
現場》文學少年讀村上春樹:蕭詒徽、盛浩偉談後青春焦慮
閱讀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