▉羨慕你還能寫詩
多年後重讀《天河撩亂》,發現小說文字處處流蕩著詩的質地。先前曾有機會專訪詩人零雨,她提及《消失在地圖上的名字》是時任時報出版公司總編輯的吳繼文主動約定要出版,實為知音。我首先請教吳繼文與詩歌的淵源。
吳繼文表情沉靜地說:「零雨是最好的中文詩人。」跟著,他才提起自己原本就寫詩,早期在零雨主編的《現代詩》發表詩作。後來因為種種機緣,才意外變成小說家。
他認為文字有太多缺陷,而詩歌寫作總是留下大量的空間,因而詩是完美的。
還寫詩嗎?吳繼文點頭,他還在寫,但沒有發表,也不會想出版詩集。吳繼文說:「讀到零雨或辛波絲卡的詩,覺得自己的詩完全沒有那樣的高度,就算了吧。」寫詩,是單單純純地寫給自己看,沒必要公諸於世。
顯然,吳繼文對自己的要求非常之嚴厲,關於文學的一切,他都是認真到底。
《天河撩亂》的最後,時澄對鴻史說:「啊,美好的一仗。恭喜你,而且羨慕你還能寫詩。」吳繼文提起羨慕寫詩這一段,講道:「那是我由衷的真心話啊。」
▉翻譯與寫作的祕密關係
 寫小說的契機,比較直接的起因,是由於楊澤與許悔之兩位。
寫小說的契機,比較直接的起因,是由於楊澤與許悔之兩位。
1993年,楊澤請他為《人間副刊》專欄寫文章,反應不俗,他才赫然發現「我原來還能夠用文字說一點故事」。後來,許悔之接掌《自由副刊》,也邀請吳繼文連載小說,《世紀末少年愛讀本》的上部便是於1995年9月初至1996年4月的連載期間內寫完的。
寫小說還有另外一些比較隱藏的層次,比如說翻譯。吳繼文選擇為吉本芭娜娜《廚房》、《哀愁與預感》、《鶇》翻譯。而眾所皆知,吉本嗜讀少女漫畫,她寫小說時,文字方面也就自然是親和的,不會用高深的文學筆觸或濃密的意象操作。這對剛開始進行日文翻譯的吳繼文來說,無疑比較容易入手。
因為翻譯吉本小說,對吳繼文寫小說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,他發現,不一定非得要有多麼深奧的文字技藝。「我開始想,原來小說也能這樣寫,也可以平易近人,但仍然可以說出動人的故事。
這似乎是寫作心態與位置的調整,小說無需一開始就站在普魯斯特、詹姆斯.喬伊斯那樣的高處。也因此,吳繼文的小說給人一種緩慢推進的親近感,讓讀者一步步貼近人物的內在風景,看見他所看見的、感覺他所感覺的。
「雖然,我寫小說的重點是放在寫什麼,但如何寫還是很重要的。」先決定結構,是吳繼文個人的儀式,比如《世紀末少年愛讀本》依附井上靖《孔子》的寫法,《天河撩亂》則是一邊引入斯文.赫定的地理報告《漂泊的湖》,另一邊則受了石黑一雄《長日將盡》啟發。
他的第三本小說十幾年來屢次重寫,就因為沒有找到一個適宜的小說結構。「一旦那個如何寫的東西出現,小說應該就會很順利地寫完。」
▉透過小說重新開啟自己
40歲以後才寫小說的原因是很複雜的,其中一個深層的原因是認識自己。吳繼文說以前在出版業時,上班是心不甘情不願的,常常蹺班,至於工作應酬什麼的,都是能躲就躲。
 吳繼文笑著說:「當時,郝明義(編按:當時任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總經理)認為我不應該再散漫下去,就帶我去打禪七。他相信,跟著惟覺老和尚打完禪七,我就會煥然一新,在工作上全力以赴,成為他的好助手。」那已經是1992年的事。
吳繼文笑著說:「當時,郝明義(編按:當時任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總經理)認為我不應該再散漫下去,就帶我去打禪七。他相信,跟著惟覺老和尚打完禪七,我就會煥然一新,在工作上全力以赴,成為他的好助手。」那已經是1992年的事。
當年兩次禪七後,吳繼文確實不一樣了。但那個不一樣,可能不在工作方面,而是自己的內在。此前的他,對待世界的方式太簡單了,對人性的複雜一無所知,也因此常常在無意之間,漫不經心地傷害了他人。
吳繼文自我反省:「別人因為我的一句話而萬劫不復,如置身地獄,我卻還自我感覺良好,以為事情就是這麼簡單清晰。」他開始不相信自己的相信,他理解到記憶是會騙人的,他所認識的自我並非真實的自我,而是被虛構出來的幻影。
打了禪七,讓吳繼文頭一次有距離地明視自己的真實樣貌,發現自己的種種缺損。而小說就是在這樣的心理背景,來到吳繼文的生命裡。他說:「我想要重新認識自己,於是寫了《天河撩亂》。」
小說是理解人心的器具,小說是打開自己的鑰匙,小說是體會他人困境的通道。他認為,小說是夢中風景,讓他看到自己,同時讓他發現,自己是虛構,世界是想像的產物。
「首先是看到,其次才是看透。而看到比看透更重要。」他語帶機鋒地說。
▉願你獲得好好活下去的勇氣
吳繼文很淡泊的樣子,給我一種因為人生到頭來沒辦法真的帶走什麼,所以無需強求的印象,也因此,他身上有著溫和而堅定的氣場。
請教他對《天河撩亂》新版在今時今日出版的期待,讀者能夠從中獲得什麼力量?吳繼文還是也無風雨也無晴地說:「好好活下去的勇氣。」
《天河撩亂》就是一扇看到自己,也看到世界的窗。寫完《天河撩亂》以後,吳繼文相信人可以賦予自己意義,人可以定義自己,而不被他人與外在世界定義,人可以不要被自己以外的定義所毀壞。
「改造自己,比改造世界實際,也更重要。」他很誠懇地說。
他提到常去陽明山步道散步,每次去風景都不一樣,變化萬千。有人就問他重複去不覺得無聊嗎?吳繼文嘴角斜揚:「我從來沒有覺得無聊的時刻,所以我很幸福。因為時間一直在走,人也一直在變化,世界從來不是固定不動的。」
如果張開內在的眼睛,好好凝視,就算只是在台灣,哪裡都沒有去,也等同於哪裡都去了,而沒有用心觀看的人即便環遊世界,也從未真正經歷過進入過。他語氣柔和但腔調堅決:「真正的祕境在自己的內心。」

▉小說不可能憑空創作
讀《天河撩亂》時,一直想起蔡明亮的《河流》與王家衛的《春光乍洩》,感覺內裡皆有相通。我好奇是否有人找吳繼文談影像改編?他點頭,已經有好幾組人馬談過,也簽約了,但因為實在太困難,至今還沒有成果。「如果真的要拍電影版,我確實很喜歡《春光乍洩》的拍法,希望《天河撩亂》是以黑白片的形式製作。」
如何經營小說的細節?吳繼文的回應是,他會將現實世界的人事物放進小說,他的小說就是這樣煉成的。「小說不可能憑空創作、無中生有,一切是有所本的,這樣才會有真實的生命力。」
另外,他也很喜歡讀日記。比如讀日本僧人圓仁在唐武宗時期寫的《入唐求法巡禮行紀》。吳繼文讚嘆地說:「他寫了整整9年,鉅細靡遺地把晚唐世俗都寫出來。歷史寫到人事物不過是簡略的幾行,但圓仁的日記會召喚出那個時代的具體風物細節。」
小說不也是這樣一回事?小說關注的是生命史,關注的是生命內在狀態的流動與變遷,關注的是怎麼樣誠實地打開自己,面對所有接踵而來的傷害。小說的精髓不在那些大可簡單幾行說明清楚的劇情走向,而是人的內心究竟是長什麼樣子,人如何迎接自身的困境,又是如何找到脫解的可能,凡此。
最後請教他對當今出版的看法。吳繼文表示,他們那個時代資源是多的,做出版相對容易一點,但當時的他其實是不合格的出版人,一點都不專業。他很正面地看待現在的出版後進:「現在是出版很困難的時代,反倒出版人和編輯變成專業,或者說非專業不可,從書的前製作業、到印製程序乃至行銷企畫等等,無一不精。」
跟吳繼文說話,就像日前與零雨交談一樣,原本殘暴的時間忽然就變得溫和了。不是時間變慢,而是時間的每一個片段都被珍惜地對待,於是人心就有了慢的可能,就有了溫柔的感受。
這一位凝望人間天河的小說家,他的溫柔,他的持續理解他者、認識人心,終將透過文字,救援此時此刻被各種撩亂圍困的人們。●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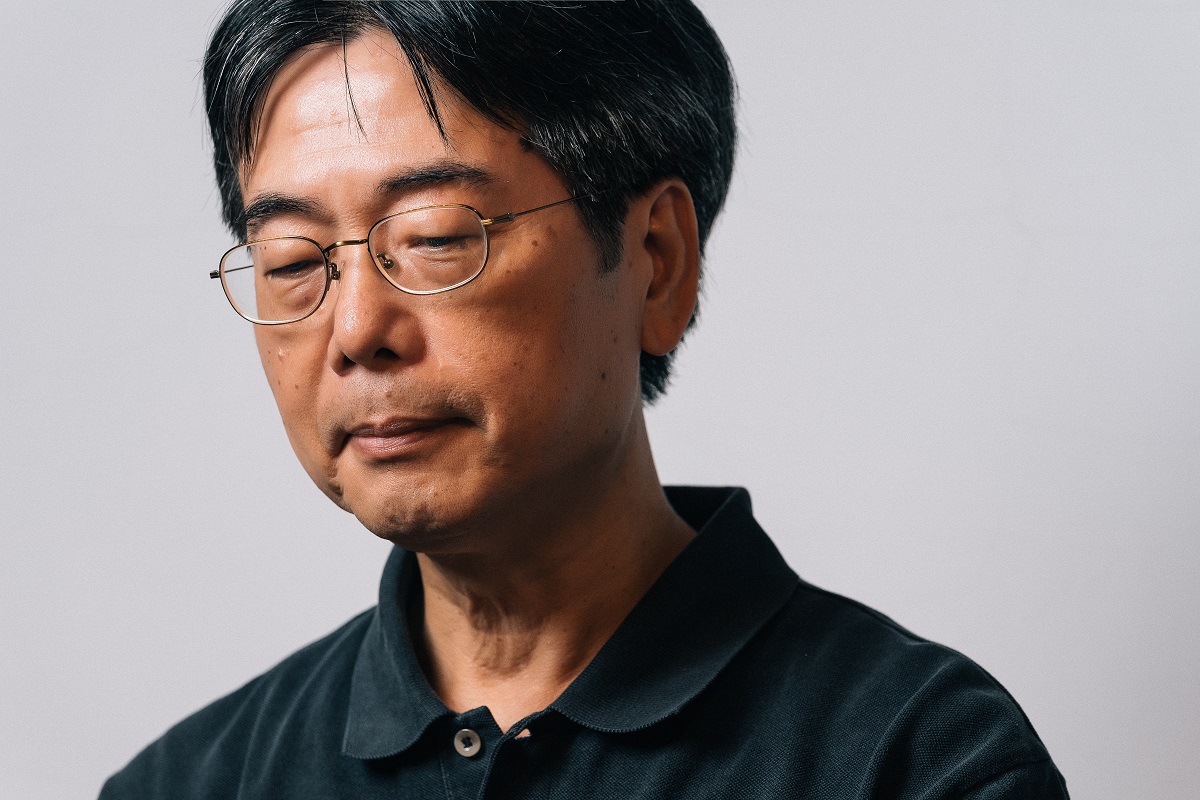
|

天河撩亂(20週年復刻版)
作者:吳繼文
出版:寶瓶文化
定價:350元
【內容簡介➤】
作者簡介:吳繼文
1955年生於南投,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畢,日本廣島大學哲學碩士;曾任聯合報副刊編輯,時報文化出版總編輯,台灣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。著有長篇小說《世紀末少年愛讀本》(聯合報〈讀書人〉年度好書)、《天河撩亂》(中國時報〈開卷〉十大好書),劇本《公園1999的一天》;譯有河口慧海《西藏旅行記》、井上靖《我的母親手記》、藤原新也《印度放浪》、中平卓馬《為何是植物圖鑑》、野野村馨《雲水一年》,以及吉本芭娜娜《廚房》、《蜥蜴》、《哀愁的預感》等多種。
|
Tags:
40歲以後寫出《世紀末少年愛讀本》、《天河撩亂》兩部名作,如今,將近20年的時間過去了,吳繼文仍在為自己的第三本小說奮戰。像是重寫自己一樣,他不斷地重寫視為最後一本小說的作品,卻始終不滿意。而在讀者引頸期盼他新小說問世之前,終究先迎來《天河撩亂》新版。Openbook閱讀誌選在位於溫州街巷弄,吳繼文最熟悉自在的咖啡館,專訪這位舉手投足都是閑靜風範的小說家。
場地提供:布拉格咖啡館
▉羨慕你還能寫詩
多年後重讀《天河撩亂》,發現小說文字處處流蕩著詩的質地。先前曾有機會專訪詩人零雨,她提及《消失在地圖上的名字》是時任時報出版公司總編輯的吳繼文主動約定要出版,實為知音。我首先請教吳繼文與詩歌的淵源。
吳繼文表情沉靜地說:「零雨是最好的中文詩人。」跟著,他才提起自己原本就寫詩,早期在零雨主編的《現代詩》發表詩作。後來因為種種機緣,才意外變成小說家。
他認為文字有太多缺陷,而詩歌寫作總是留下大量的空間,因而詩是完美的。
還寫詩嗎?吳繼文點頭,他還在寫,但沒有發表,也不會想出版詩集。吳繼文說:「讀到零雨或辛波絲卡的詩,覺得自己的詩完全沒有那樣的高度,就算了吧。」寫詩,是單單純純地寫給自己看,沒必要公諸於世。
顯然,吳繼文對自己的要求非常之嚴厲,關於文學的一切,他都是認真到底。
《天河撩亂》的最後,時澄對鴻史說:「啊,美好的一仗。恭喜你,而且羨慕你還能寫詩。」吳繼文提起羨慕寫詩這一段,講道:「那是我由衷的真心話啊。」
▉翻譯與寫作的祕密關係
1993年,楊澤請他為《人間副刊》專欄寫文章,反應不俗,他才赫然發現「我原來還能夠用文字說一點故事」。後來,許悔之接掌《自由副刊》,也邀請吳繼文連載小說,《世紀末少年愛讀本》的上部便是於1995年9月初至1996年4月的連載期間內寫完的。
寫小說還有另外一些比較隱藏的層次,比如說翻譯。吳繼文選擇為吉本芭娜娜《廚房》、《哀愁與預感》、《鶇》翻譯。而眾所皆知,吉本嗜讀少女漫畫,她寫小說時,文字方面也就自然是親和的,不會用高深的文學筆觸或濃密的意象操作。這對剛開始進行日文翻譯的吳繼文來說,無疑比較容易入手。
因為翻譯吉本小說,對吳繼文寫小說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,他發現,不一定非得要有多麼深奧的文字技藝。「我開始想,原來小說也能這樣寫,也可以平易近人,但仍然可以說出動人的故事。
這似乎是寫作心態與位置的調整,小說無需一開始就站在普魯斯特、詹姆斯.喬伊斯那樣的高處。也因此,吳繼文的小說給人一種緩慢推進的親近感,讓讀者一步步貼近人物的內在風景,看見他所看見的、感覺他所感覺的。
「雖然,我寫小說的重點是放在寫什麼,但如何寫還是很重要的。」先決定結構,是吳繼文個人的儀式,比如《世紀末少年愛讀本》依附井上靖《孔子》的寫法,《天河撩亂》則是一邊引入斯文.赫定的地理報告《漂泊的湖》,另一邊則受了石黑一雄《長日將盡》啟發。
他的第三本小說十幾年來屢次重寫,就因為沒有找到一個適宜的小說結構。「一旦那個如何寫的東西出現,小說應該就會很順利地寫完。」
▉透過小說重新開啟自己
40歲以後才寫小說的原因是很複雜的,其中一個深層的原因是認識自己。吳繼文說以前在出版業時,上班是心不甘情不願的,常常蹺班,至於工作應酬什麼的,都是能躲就躲。
當年兩次禪七後,吳繼文確實不一樣了。但那個不一樣,可能不在工作方面,而是自己的內在。此前的他,對待世界的方式太簡單了,對人性的複雜一無所知,也因此常常在無意之間,漫不經心地傷害了他人。
吳繼文自我反省:「別人因為我的一句話而萬劫不復,如置身地獄,我卻還自我感覺良好,以為事情就是這麼簡單清晰。」他開始不相信自己的相信,他理解到記憶是會騙人的,他所認識的自我並非真實的自我,而是被虛構出來的幻影。
打了禪七,讓吳繼文頭一次有距離地明視自己的真實樣貌,發現自己的種種缺損。而小說就是在這樣的心理背景,來到吳繼文的生命裡。他說:「我想要重新認識自己,於是寫了《天河撩亂》。」
小說是理解人心的器具,小說是打開自己的鑰匙,小說是體會他人困境的通道。他認為,小說是夢中風景,讓他看到自己,同時讓他發現,自己是虛構,世界是想像的產物。
「首先是看到,其次才是看透。而看到比看透更重要。」他語帶機鋒地說。
▉願你獲得好好活下去的勇氣
吳繼文很淡泊的樣子,給我一種因為人生到頭來沒辦法真的帶走什麼,所以無需強求的印象,也因此,他身上有著溫和而堅定的氣場。
請教他對《天河撩亂》新版在今時今日出版的期待,讀者能夠從中獲得什麼力量?吳繼文還是也無風雨也無晴地說:「好好活下去的勇氣。」
《天河撩亂》就是一扇看到自己,也看到世界的窗。寫完《天河撩亂》以後,吳繼文相信人可以賦予自己意義,人可以定義自己,而不被他人與外在世界定義,人可以不要被自己以外的定義所毀壞。
「改造自己,比改造世界實際,也更重要。」他很誠懇地說。
他提到常去陽明山步道散步,每次去風景都不一樣,變化萬千。有人就問他重複去不覺得無聊嗎?吳繼文嘴角斜揚:「我從來沒有覺得無聊的時刻,所以我很幸福。因為時間一直在走,人也一直在變化,世界從來不是固定不動的。」
如果張開內在的眼睛,好好凝視,就算只是在台灣,哪裡都沒有去,也等同於哪裡都去了,而沒有用心觀看的人即便環遊世界,也從未真正經歷過進入過。他語氣柔和但腔調堅決:「真正的祕境在自己的內心。」
▉小說不可能憑空創作
讀《天河撩亂》時,一直想起蔡明亮的《河流》與王家衛的《春光乍洩》,感覺內裡皆有相通。我好奇是否有人找吳繼文談影像改編?他點頭,已經有好幾組人馬談過,也簽約了,但因為實在太困難,至今還沒有成果。「如果真的要拍電影版,我確實很喜歡《春光乍洩》的拍法,希望《天河撩亂》是以黑白片的形式製作。」
如何經營小說的細節?吳繼文的回應是,他會將現實世界的人事物放進小說,他的小說就是這樣煉成的。「小說不可能憑空創作、無中生有,一切是有所本的,這樣才會有真實的生命力。」
另外,他也很喜歡讀日記。比如讀日本僧人圓仁在唐武宗時期寫的《入唐求法巡禮行紀》。吳繼文讚嘆地說:「他寫了整整9年,鉅細靡遺地把晚唐世俗都寫出來。歷史寫到人事物不過是簡略的幾行,但圓仁的日記會召喚出那個時代的具體風物細節。」
小說不也是這樣一回事?小說關注的是生命史,關注的是生命內在狀態的流動與變遷,關注的是怎麼樣誠實地打開自己,面對所有接踵而來的傷害。小說的精髓不在那些大可簡單幾行說明清楚的劇情走向,而是人的內心究竟是長什麼樣子,人如何迎接自身的困境,又是如何找到脫解的可能,凡此。
最後請教他對當今出版的看法。吳繼文表示,他們那個時代資源是多的,做出版相對容易一點,但當時的他其實是不合格的出版人,一點都不專業。他很正面地看待現在的出版後進:「現在是出版很困難的時代,反倒出版人和編輯變成專業,或者說非專業不可,從書的前製作業、到印製程序乃至行銷企畫等等,無一不精。」
跟吳繼文說話,就像日前與零雨交談一樣,原本殘暴的時間忽然就變得溫和了。不是時間變慢,而是時間的每一個片段都被珍惜地對待,於是人心就有了慢的可能,就有了溫柔的感受。
這一位凝望人間天河的小說家,他的溫柔,他的持續理解他者、認識人心,終將透過文字,救援此時此刻被各種撩亂圍困的人們。●
天河撩亂(20週年復刻版)
作者:吳繼文
出版:寶瓶文化
定價:350元
【內容簡介➤】
作者簡介:吳繼文
1955年生於南投,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畢,日本廣島大學哲學碩士;曾任聯合報副刊編輯,時報文化出版總編輯,台灣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。著有長篇小說《世紀末少年愛讀本》(聯合報〈讀書人〉年度好書)、《天河撩亂》(中國時報〈開卷〉十大好書),劇本《公園1999的一天》;譯有河口慧海《西藏旅行記》、井上靖《我的母親手記》、藤原新也《印度放浪》、中平卓馬《為何是植物圖鑑》、野野村馨《雲水一年》,以及吉本芭娜娜《廚房》、《蜥蜴》、《哀愁的預感》等多種。
手指點一下,您支持的每一分錢
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
【Openbook國際書展參戰(;・`д・´)】
2/6(五)歡迎加入玩耍!•̀.̫•́✧書寫、行動與反思:和島嶼互動的幾種方式
閱讀通信 vol.367》如果我在晚上九點敲響你的房門
延伸閱讀
書評》曖昧處更分明:如何同志,怎樣文學
*** 閱讀更多
書評》視覺霸權時代的小說家反擊:評《文藝春秋》
閱讀更多
專訪》你的廁所就是我的廁所——許悔之、盛浩偉,把手牽起來了
近來,為反對性別歧視,智利男性發起「織毛衣的男人」活動,傳達男人也有溫柔、細膩。而文學不也是一種編織嗎?於是,Openbook編輯部邀請兩位「暖男」... 閱讀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