座談會一開場,譚蕙芸就分享道:「我一直記得在台北的第一場新書分享會,我講到家庭,那些在座的女性,特別一些是很漂亮的中年女性,眼睛裡都是淚汪汪的看著我。」
「我就想,發生什麼事?為什麼有個共通的感覺,這麼委屈?」譚蕙芸觀察,雖然自己家庭的故事是特殊的,但太多「女兒們」的委屈,卻似乎有著類似的根源。
可以說,這場座談會兩位講者的新書,都是關於身為女兒的種種委屈,都是要回答家庭內究竟「發生什麼事」。然而與此同時,兩人對談的內容也都不時回應到另一個主題:身為女兒,面對這些委屈,她們又如何長出自保的力量?
譚蕙芸是香港的資深記者與大學教師,新作《家鎖:華人家庭這個巨獸》回頭探索自己家庭的故事。她「嘗試用一種既抽離又不失主觀的視覺,去檢視這個家庭到底走了一條怎樣的路」——一個小康的家庭怎樣走上這條路,竟將罹患精神疾病的哥哥關在家中20餘年,成為父母嚴守的祕密?這又如何牽動身為女兒的她和這個家庭的關係?
與她對談的張慧慈則來自台灣的藍領家庭,是家中長女,新書《長女病:我們不是天生愛扛責任,台灣跨世代女兒的故事》揉合了自己和十餘位長女們的故事,談論從「在家中必須照顧弟妹」到「在職場上繼續害怕讓人失望」等種種難關。
在提及寫作的企圖時,張慧慈所用的關鍵詞也同樣是「委屈」,她希望這個社會比較開放地去討論家庭,至少家庭裡面受苦的人不再只能是默默委屈。委屈需要訴說,也需要解決,張慧慈接著說:「不只是吐槽、不只是抱怨,而是想出一些辦法,讓大家都過得比較好。」
➤不能不回家,但要能隨時撤退或逃離
女兒們經常面臨的委屈之一,是被迫回到家裡承擔責任、卻又對於各種事務沒有發言權的窘境。譚蕙芸回顧,從父母決定把患病的哥哥「藏起來」開始,一路到自己把移民加拿大的家人接回香港居住,這個過程中她常遇到的狀況便是:「長子失能了,小女兒要扛的時候,大家都說『不行,小女兒怎麼能夠指揮我們!』,所以我遇到的反彈是很大的。」
女兒們必須承擔,但又不能指揮、甚至沒有發言權,或許已經是太典型的故事。張慧慈如此描述許多受訪者的共同經驗:「她們可能跟哥哥、弟弟一樣,都一直在追求自己的人生夢想。可是當家中長輩生病,需要陪病、照顧的時候,她們會發現爸媽只期待女兒回家,而且是有點強硬的,要求女兒放下工作。當女兒說『可是我需要賺錢』的時候,父母就會說:『我有準備錢、準備房子,你要回家』。」
那為什麼不找兒子承擔?張慧慈分析,原因是多重的,「如果她們說哥哥、弟弟也可以帶你去看醫生,父母就會說『他不懂』。可是這個『不懂』背後是一種偏見,認為『女生比較細心』。同時,他們也認為『女兒就是應該要回來照顧爸媽』,所以兒子的『不懂』背後,是女兒必須要犧牲。」
但回家之後如果再也不能抽身,對體力、精神都是很大的消磨。譚蕙芸以自身經驗為例,分享她觀察到的一個問題根源或許是:華人的情感表達習慣。她在書裡寫到,父親屢屢調侃身為主婦的母親「對世界大事一無所知,只知道廚房裡的事。」講座上她也進一步分享,「到今天,我們家外傭都常常跟我投訴,為什麼我爸爸到90多歲,都還在以責罵表達他對我媽媽的愛。我媽媽被他罵了有點不開心,但又還是好像給他罵才安心。」
「我的書出版後有一個教授跟我說,華人家庭那種用罵的、貶低、控制的來代替關愛,這是他們表達的方法」,譚慧芸苦笑著說,「我們華人都不知道是從哪裡學到這一點的,『吵架都是愛』。」
既然經常必須處在消耗心神的環境與關係中,女兒們能夠做的第一步,就是保有物理上暫時撤退的可能。為了拉開距離,張慧慈自陳她和妹妹所採行的策略有點奢侈——「我們都在離家裡很近的地方租房子。老實說這樣很花錢,如果拿房租去投資股票,也許賺更多。」對於這筆必須額外花費的成本,她說得很直白:「但是我知道如果沒有去租那個房子,我說不定會去跳樓。」
關於物理距離,譚蕙芸也用了一個十分具象的描述:她要能隨時從家裡「奔去旅館」。對她而言,這不只是幫自己拉開距離,也是讓自己回到家中時更有底氣。
「至少我能夠奔去旅館,不用依靠他們。很多年輕人會擔心自己沒有辦法改變現況,但是如果你能夠有離開家庭獨自生活的資源和能力,證明給家人看,至少自己過的生活是好的,那麼你說話的聲音會大一點。」
「你是女性,這大概沒辦法改變」,譚蕙芸進一步解釋:「假如你是男人,他們(父母)可能會聽你的,是老男人的話,更會聽你的,對吧?我們的弱勢已經沒辦法改變,但是至少我賺了錢,能夠說話,他就會感覺你不像以前這麼好叫。」
➤切開有毒的關係與觀念
就此而言,拉開距離是雙向的,不只要自己找到撤退的辦法,也要想辦法不再讓家人覺得自己「像以前那麼好叫」。畢竟,這社會上有太多會讓長輩們覺得女兒應該要「很好叫」的推力了。
張慧慈分享,長輩們如何鞏固、強化這樣的認知:「有些父母手機上的群組真的很可怕。我媽媽之前每天都轉貼社群上跟『孝』有關的東西,例如什麼巴菲特說要孝順、富蘭克林說要孝順,發一個不知道是誰的頭像說『要孝順!』」
 這甚至不只發生在網路上,張慧慈接著說,有一次妹妹透露,她會不時跟著媽媽一起去便利商店,因為媽媽的朋友們都會約在便利商店碰面、聊天。妹妹發現,媽媽的朋友們會灌輸她:「妳如果沒辦法控制小孩,小孩就會不孝,他們以後就會拋棄你。所以妳要回去跟他們要錢,要叫他們帶你出去玩。」
這甚至不只發生在網路上,張慧慈接著說,有一次妹妹透露,她會不時跟著媽媽一起去便利商店,因為媽媽的朋友們都會約在便利商店碰面、聊天。妹妹發現,媽媽的朋友們會灌輸她:「妳如果沒辦法控制小孩,小孩就會不孝,他們以後就會拋棄你。所以妳要回去跟他們要錢,要叫他們帶你出去玩。」
「我覺得這真的是有毒的關係!」後來,張慧慈和妹妹決定要媽媽去找工作,「我媽在40歲後就沒有工作,50幾歲的時候我們逼媽媽再回去上班」,說到這裡,張慧慈語氣中帶著笑意,「我媽從此以後不傳孝道的東西給我們了,她每天下班回來,都跟我們講同事的壞話,我覺得她這樣心理狀態還比較健康。」
張慧慈不只是嘗試自己和家人拉開距離,也從母親那頭下手,讓她也能和這些「有毒」的關係網絡、觀念拉開距離。
➤愈到異國他界,愈寄情傳統文化
然而,並非人人都能斷開道德規訓的束縛。譚蕙芸身為加拿大華僑子女,感受更深的是,父母因為移民經驗,反而變得愈來愈頑固和保守。「我爸爸在香港的時候明明很西化,穿西裝、打領帶。到了加拿大,卻開始畫山水、寫書法,到了老外的地方,突然改變了自我認同,更傾向『傳統中國』。」
同樣的認同需求不只促成了譚蕙芸的父親對傳統書畫的興趣,更形塑了父母認定女兒必須結婚、必須盡到照顧的責任。而且明明搬到了精神疾病汙名淡化、照顧資源也更豐富的加拿大,他們反而更堅持把罹患思覺失調的兒子關在家中,「因為他覺得自己要透過這一套文化實踐,來證明自己的身分。他不能夠變成老外,所以有一個反彈,回到家裡他只會更傳統,不能夠更開放。」
張慧慈或許能夠讓媽媽不再去便利商店,但譚蕙芸卻無從說服父母「變成老外」。這時,保護她的是另一種資本,讓自己可以辨認出這種想像中的傳統,也與之保持相當的距離。

這種資本,正是來自她在教育、職場上的歷練。「幸好我爸媽是到我差不多中年,才要求我回去照顧,不是讓我的黃金歲月都用在照顧他們。我在已經累積所有資源之後,才進入這個誇張的長照考驗。」
譚蕙芸累積的資源不只是金錢,也包含了各種知識與資歷,「那個時候我已經累積了一定的文化資本。就像慧慈讀到碩士、博士,是整個家族裡讀書最多的人。而我當過記者嘛,知道外面的世界是甚麼樣子,不會被他們說那些話『騙到』。」
譚蕙芸分析,金錢的資本讓她們有條件拉出適度的物理距離,喘一口氣;而文化的資本則讓她們得以拉開必須的心理距離,不致迷失。
面對委屈,女兒們除了拉開距離、劃下界線,還要讓自己過得更好、變得強大一點。張慧慈提及諮商對於自己面對職場困難與家庭關係張力的助益;而譚蕙芸除了去諮商,也以能扛起父親的體重為目標健身重訓。
或者,就如同譚蕙芸在講座結尾時所說的:「這個世界大概是很喜歡讓女性進入自怨自憐的心態吧,而我們需要慢慢走出來。」●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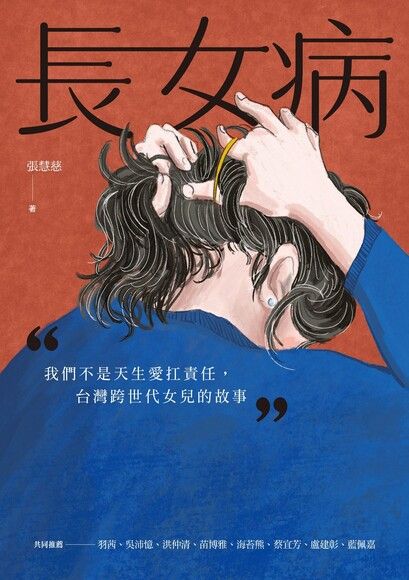 長女病:我們不是天生愛扛責任,台灣跨世代女兒的故事 長女病:我們不是天生愛扛責任,台灣跨世代女兒的故事
作者:張慧慈
出版:游擊文化
定價:450元
【內容簡介➤】
|
|
作者簡介:張慧慈(小花媽)
1988年生,長女。畢業於台大社會所、清大人文與社會學系、板橋高中,是個在北部長大的北港孩子。雙子座的靈魂,註定無法在一處停留。曾在政治圈工作、在總統府當文稿幕僚,也曾踏入傳統產業,在越南擔任台幹,亦曾在藝文圈工作,去國外行銷台灣的電影,目前在住宅產業工作。
喜歡說話跟寫東西。最近在研究命理,夢想成為命理大師,讓更多人想跟她講話。著有《咬一口馬克思的水煎包》、《乾脆躺平算了》。經營臉書粉專「小花媽」,並有Podcast節目《南臺灣大姑娘》。
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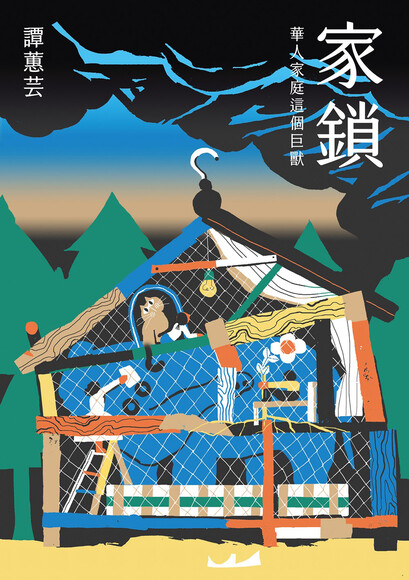 家鎖:華人家庭這個巨獸 家鎖:華人家庭這個巨獸
作者:譚蕙芸
出版:春山出版
定價:490元
【內容簡介➤】
|
|
作者簡介:譚蕙芸(Vivian Tam)
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高級講師,獨立記者。著有《天愈黑,星愈亮:反修例運動的人和事》、《文字欲:回應時代的特寫新聞》等書。
|
Tags:
《長女病》作者張慧慈(左)及《家鎖》作者譚蕙芸。
今年出版的《長女病:我們不是天生愛扛責任,台灣跨世代女兒的故事》與《家鎖:華人家庭這個巨獸》,都是作者從自身經歷書寫家庭關係及照顧議題的作品,面市後同樣引起許多讀者的共鳴與回響。兩位作者張慧慈、譚蕙芸在各自的新書分享會上,經常收到讀者回饋時推薦對方的書籍。近期,原本互不相識的兩人讀完彼此的新書後,都大呼這兩本書相當適合一起閱讀參照,也十分期待相見對話,因而促成了這場座談會的舉辦。本文是座談側記。
座談會一開場,譚蕙芸就分享道:「我一直記得在台北的第一場新書分享會,我講到家庭,那些在座的女性,特別一些是很漂亮的中年女性,眼睛裡都是淚汪汪的看著我。」
「我就想,發生什麼事?為什麼有個共通的感覺,這麼委屈?」譚蕙芸觀察,雖然自己家庭的故事是特殊的,但太多「女兒們」的委屈,卻似乎有著類似的根源。
可以說,這場座談會兩位講者的新書,都是關於身為女兒的種種委屈,都是要回答家庭內究竟「發生什麼事」。然而與此同時,兩人對談的內容也都不時回應到另一個主題:身為女兒,面對這些委屈,她們又如何長出自保的力量?
譚蕙芸是香港的資深記者與大學教師,新作《家鎖:華人家庭這個巨獸》回頭探索自己家庭的故事。她「嘗試用一種既抽離又不失主觀的視覺,去檢視這個家庭到底走了一條怎樣的路」——一個小康的家庭怎樣走上這條路,竟將罹患精神疾病的哥哥關在家中20餘年,成為父母嚴守的祕密?這又如何牽動身為女兒的她和這個家庭的關係?
與她對談的張慧慈則來自台灣的藍領家庭,是家中長女,新書《長女病:我們不是天生愛扛責任,台灣跨世代女兒的故事》揉合了自己和十餘位長女們的故事,談論從「在家中必須照顧弟妹」到「在職場上繼續害怕讓人失望」等種種難關。
在提及寫作的企圖時,張慧慈所用的關鍵詞也同樣是「委屈」,她希望這個社會比較開放地去討論家庭,至少家庭裡面受苦的人不再只能是默默委屈。委屈需要訴說,也需要解決,張慧慈接著說:「不只是吐槽、不只是抱怨,而是想出一些辦法,讓大家都過得比較好。」
➤不能不回家,但要能隨時撤退或逃離
女兒們經常面臨的委屈之一,是被迫回到家裡承擔責任、卻又對於各種事務沒有發言權的窘境。譚蕙芸回顧,從父母決定把患病的哥哥「藏起來」開始,一路到自己把移民加拿大的家人接回香港居住,這個過程中她常遇到的狀況便是:「長子失能了,小女兒要扛的時候,大家都說『不行,小女兒怎麼能夠指揮我們!』,所以我遇到的反彈是很大的。」
女兒們必須承擔,但又不能指揮、甚至沒有發言權,或許已經是太典型的故事。張慧慈如此描述許多受訪者的共同經驗:「她們可能跟哥哥、弟弟一樣,都一直在追求自己的人生夢想。可是當家中長輩生病,需要陪病、照顧的時候,她們會發現爸媽只期待女兒回家,而且是有點強硬的,要求女兒放下工作。當女兒說『可是我需要賺錢』的時候,父母就會說:『我有準備錢、準備房子,你要回家』。」
那為什麼不找兒子承擔?張慧慈分析,原因是多重的,「如果她們說哥哥、弟弟也可以帶你去看醫生,父母就會說『他不懂』。可是這個『不懂』背後是一種偏見,認為『女生比較細心』。同時,他們也認為『女兒就是應該要回來照顧爸媽』,所以兒子的『不懂』背後,是女兒必須要犧牲。」
但回家之後如果再也不能抽身,對體力、精神都是很大的消磨。譚蕙芸以自身經驗為例,分享她觀察到的一個問題根源或許是:華人的情感表達習慣。她在書裡寫到,父親屢屢調侃身為主婦的母親「對世界大事一無所知,只知道廚房裡的事。」講座上她也進一步分享,「到今天,我們家外傭都常常跟我投訴,為什麼我爸爸到90多歲,都還在以責罵表達他對我媽媽的愛。我媽媽被他罵了有點不開心,但又還是好像給他罵才安心。」
「我的書出版後有一個教授跟我說,華人家庭那種用罵的、貶低、控制的來代替關愛,這是他們表達的方法」,譚慧芸苦笑著說,「我們華人都不知道是從哪裡學到這一點的,『吵架都是愛』。」
既然經常必須處在消耗心神的環境與關係中,女兒們能夠做的第一步,就是保有物理上暫時撤退的可能。為了拉開距離,張慧慈自陳她和妹妹所採行的策略有點奢侈——「我們都在離家裡很近的地方租房子。老實說這樣很花錢,如果拿房租去投資股票,也許賺更多。」對於這筆必須額外花費的成本,她說得很直白:「但是我知道如果沒有去租那個房子,我說不定會去跳樓。」
關於物理距離,譚蕙芸也用了一個十分具象的描述:她要能隨時從家裡「奔去旅館」。對她而言,這不只是幫自己拉開距離,也是讓自己回到家中時更有底氣。
「至少我能夠奔去旅館,不用依靠他們。很多年輕人會擔心自己沒有辦法改變現況,但是如果你能夠有離開家庭獨自生活的資源和能力,證明給家人看,至少自己過的生活是好的,那麼你說話的聲音會大一點。」
「你是女性,這大概沒辦法改變」,譚蕙芸進一步解釋:「假如你是男人,他們(父母)可能會聽你的,是老男人的話,更會聽你的,對吧?我們的弱勢已經沒辦法改變,但是至少我賺了錢,能夠說話,他就會感覺你不像以前這麼好叫。」
➤切開有毒的關係與觀念
就此而言,拉開距離是雙向的,不只要自己找到撤退的辦法,也要想辦法不再讓家人覺得自己「像以前那麼好叫」。畢竟,這社會上有太多會讓長輩們覺得女兒應該要「很好叫」的推力了。
張慧慈分享,長輩們如何鞏固、強化這樣的認知:「有些父母手機上的群組真的很可怕。我媽媽之前每天都轉貼社群上跟『孝』有關的東西,例如什麼巴菲特說要孝順、富蘭克林說要孝順,發一個不知道是誰的頭像說『要孝順!』」
「我覺得這真的是有毒的關係!」後來,張慧慈和妹妹決定要媽媽去找工作,「我媽在40歲後就沒有工作,50幾歲的時候我們逼媽媽再回去上班」,說到這裡,張慧慈語氣中帶著笑意,「我媽從此以後不傳孝道的東西給我們了,她每天下班回來,都跟我們講同事的壞話,我覺得她這樣心理狀態還比較健康。」
張慧慈不只是嘗試自己和家人拉開距離,也從母親那頭下手,讓她也能和這些「有毒」的關係網絡、觀念拉開距離。
➤愈到異國他界,愈寄情傳統文化
然而,並非人人都能斷開道德規訓的束縛。譚蕙芸身為加拿大華僑子女,感受更深的是,父母因為移民經驗,反而變得愈來愈頑固和保守。「我爸爸在香港的時候明明很西化,穿西裝、打領帶。到了加拿大,卻開始畫山水、寫書法,到了老外的地方,突然改變了自我認同,更傾向『傳統中國』。」
同樣的認同需求不只促成了譚蕙芸的父親對傳統書畫的興趣,更形塑了父母認定女兒必須結婚、必須盡到照顧的責任。而且明明搬到了精神疾病汙名淡化、照顧資源也更豐富的加拿大,他們反而更堅持把罹患思覺失調的兒子關在家中,「因為他覺得自己要透過這一套文化實踐,來證明自己的身分。他不能夠變成老外,所以有一個反彈,回到家裡他只會更傳統,不能夠更開放。」
張慧慈或許能夠讓媽媽不再去便利商店,但譚蕙芸卻無從說服父母「變成老外」。這時,保護她的是另一種資本,讓自己可以辨認出這種想像中的傳統,也與之保持相當的距離。
這種資本,正是來自她在教育、職場上的歷練。「幸好我爸媽是到我差不多中年,才要求我回去照顧,不是讓我的黃金歲月都用在照顧他們。我在已經累積所有資源之後,才進入這個誇張的長照考驗。」
譚蕙芸累積的資源不只是金錢,也包含了各種知識與資歷,「那個時候我已經累積了一定的文化資本。就像慧慈讀到碩士、博士,是整個家族裡讀書最多的人。而我當過記者嘛,知道外面的世界是甚麼樣子,不會被他們說那些話『騙到』。」
譚蕙芸分析,金錢的資本讓她們有條件拉出適度的物理距離,喘一口氣;而文化的資本則讓她們得以拉開必須的心理距離,不致迷失。
面對委屈,女兒們除了拉開距離、劃下界線,還要讓自己過得更好、變得強大一點。張慧慈提及諮商對於自己面對職場困難與家庭關係張力的助益;而譚蕙芸除了去諮商,也以能扛起父親的體重為目標健身重訓。
或者,就如同譚蕙芸在講座結尾時所說的:「這個世界大概是很喜歡讓女性進入自怨自憐的心態吧,而我們需要慢慢走出來。」●
作者:張慧慈
出版:游擊文化
定價:450元
【內容簡介➤】
作者簡介:張慧慈(小花媽)
1988年生,長女。畢業於台大社會所、清大人文與社會學系、板橋高中,是個在北部長大的北港孩子。雙子座的靈魂,註定無法在一處停留。曾在政治圈工作、在總統府當文稿幕僚,也曾踏入傳統產業,在越南擔任台幹,亦曾在藝文圈工作,去國外行銷台灣的電影,目前在住宅產業工作。
喜歡說話跟寫東西。最近在研究命理,夢想成為命理大師,讓更多人想跟她講話。著有《咬一口馬克思的水煎包》、《乾脆躺平算了》。經營臉書粉專「小花媽」,並有Podcast節目《南臺灣大姑娘》。
作者:譚蕙芸
出版:春山出版
定價:490元
【內容簡介➤】
作者簡介:譚蕙芸(Vivian Tam)
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高級講師,獨立記者。著有《天愈黑,星愈亮:反修例運動的人和事》、《文字欲:回應時代的特寫新聞》等書。
手指點一下,您支持的每一分錢
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
【Openbook國際書展參戰(;・`д・´)】
2/6(五)歡迎加入玩耍!•̀.̫•́✧書寫、行動與反思:和島嶼互動的幾種方式
閱讀通信 vol.367》如果我在晚上九點敲響你的房門
延伸閱讀
書單》愛與傷的總和,83本關於家庭、創傷與和解的書籍
閱讀更多
愛與傷的總和》站在兒時的創傷前:作家曾稔育、醫師吳佳璇談親職化兒童與缺席的親情
在以「家」為中心,思考不同的當代創傷情境時,兒童人權與福利已從原先消極的關注家暴與受虐兒童,漸漸擴展到積極的關懷兒童是否有個幸福應得的童年。與此相應的,... 閱讀更多
人物》聽見零雨,也聽見自己:羅思容《女兒的九十九種藍》唱出女性的生命潮汐
編按:2022年詩人零雨出版詩集《女兒》,收錄10首描繪普世女性境遇的敘事詩,當年即獲得Openbook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。今(2025)年零雨更榮獲美國「... 閱讀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