➤歌曲是因接觸世界而生的
謝子凡:
先謝謝郅忻,《憶曲心聲》讓我想起許多音樂帶來的美好時光,腦袋叮叮咚咚響個不停,像是按下琴鍵後,震動於空氣中的音符撞擊了各種物件,又分別綻放出自己的音色。
最近我正好在讀是枝裕和導演的書《我在拍電影時思考的事》,裡頭提到拍 攝歌手Cocco的紀錄片時,導演心裡的感受:「歌曲是因接觸世界而生的」。這句話用以形容《憶曲心聲》也是恰恰好的。郅忻的文字因歌曲而生,也收攏了當下的內心風景,是作者與世界的切面產生的真情互動。
攝歌手Cocco的紀錄片時,導演心裡的感受:「歌曲是因接觸世界而生的」。這句話用以形容《憶曲心聲》也是恰恰好的。郅忻的文字因歌曲而生,也收攏了當下的內心風景,是作者與世界的切面產生的真情互動。
我有一種感覺,郅忻的心像是精巧的玻璃風鈴,此書即是玲瓏心腸敲出的長長曲子。說是玻璃風鈴,是因為郅忻說起家人,無論是長輩或孩子,皆自然不保留,即使提起傷逝,情感亦透明可親。
要將對某首歌的深情化為篇章,實屬不易。歌曲有詞曲原本設定的意境,又需與自己所感做結合,想請郅忻分享一下這捕捉的手藝。是因為歌曲牽動了感情,進而召喚出場景;還是在此情此景之下,聽見了迴盪的背景音呢?
張郅忻:
謝謝子凡的閱讀與聆聽。聲音,確實是不可捉摸,卻又沒有什麼比它更能表達存在於內心深處、難以言喻的觸動與情緒。《憶曲心聲》原是我在人間福報副刊的專欄,最初是想記錄兒時聽過的客家歌曲與念謠,那時父喪不久,總覺得四方歌聲都有父親的影子。我才醒悟,儘管曾有怨懟,我依舊還是那個依賴父親的小女孩。於是,專欄也開始寫了與父親回憶有關的歌。如父親臨終時我才知曉的〈給你呆呆〉,還有父親拿起麥克風必唱的張雨生〈大海〉。關於子凡的提問,似乎是兩者都有。有時是點播記憶中的歌,進而召喚情感。有時則是忽然在某個時刻,耳邊響起舊時的樂音。
我們在聆聽一首歌時,總是會想起某一個人或第一次聽見這首歌的場景。這使我們經常「誤讀」一首歌,然後在漫漫的成長之途中重新認識它。比如子凡在〈與你的相對位置〉中,提到哥哥在上舖哼著羅大佑的〈亞細亞的孤兒〉。年紀尚小的我,是聽小叔叔播放的,懵懂間跟著哼唱「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」,只是當時怎會知道那玩具竟如此沉重?但,這種「誤讀」讓一首歌對不同聆聽者有了殊異體驗。不知道子凡如何看待這種「誤讀」或「誤聽」?
➤誤讀之外,讀者的江湖道義
謝子凡:
誤讀經常發生,甚至是必然的。
如我輩聽團仔必聽的1976,每每唱起名曲之一〈方向感〉的時候,全場都會跟著嘶吼:「也許你該學習相信自己的方向感」,現場幾成暴動狀態。我相信這時大家心中想的,是在徬徨中想抓住些什麼的自己。
但主唱阿凱曾半開玩笑地說這原本是一首渣男之歌,本意是在感情中,「我」不想擔負指南針的角色,你去尋找自己的方向感吧。
有名的誤讀還有工人皇帝Bruce Springsteen,一首激昂的〈Born in the USA〉曾被美國政治人物選為競選歌曲。然而歌詞所述的是藉由一名越戰退伍軍人之口,控訴這塊土地的種種不公,Demo帶的初版編曲更是幽幽怨怨如泣如訴。後來發行時採取與歌詞相反的音樂意象,頗有反諷意味。所以當有人眼神閃亮地唱著這首歌時,我都覺得饒富趣味。
我又接著想到,是枝裕和帶著《幻之光》參加法國的南特三洲影展時,觀眾在映後座談會上熱烈討論「究竟從哪裡開始是夢境?」,當導演想要開口時,還被觀眾制止,「導演請先別說」,而觀眾繼續各自訴說自己的看法。
總之誤讀看來不可避免。而抽離出來看他人的各種誤讀,再對照作者原意,也成另一種有意思的風景。
但作為一個讀者、聽眾,在相信自己的感受之餘,同時努力去靠近作者,也是身為讀者的江湖道義(笑),我是這麼覺得的。郅忻的看法又是怎麼樣的呢?
郅忻在這本書裡採取了非常溫柔的切入點,接下來這個問題是我自己近期的思索,剛好有這難得的機會,便大膽提問:在親族的感情上,有沒有可能——可以恨,所以其他部分才可以愛?許多感情就是糾結在又愛又恨,所以處理不來。想要愛他,但又有地方是絕對不想原諒的。想要恨他,一些自己相信是愛的記憶卻也揮之不去。我們在處理生命難題時,有沒有可能切割開來,分開談愛與恨(或是愛與不愛)?
➤指認,然後到下一個地方
張郅忻:
謝謝子凡分享如此精彩的誤讀經驗。我一邊聽著這些歌曲,一邊重新咀嚼子凡的文字。當我放大了耳朵,才聽見〈我和我追逐的垃圾車〉中多層次的聲音。那些圍繞生活的聲響,如租屋處隔壁吃著鹹酥雞的聲音、辦公室裡細碎交談聲,最終以垃圾車播放的「少女的祈禱」作為結束。我彷彿走進一個精心佈置的聲響世界,在字裡行間尋覓作者的身影。
對於子凡詢問在書寫中如何處理關於親族的「愛」與「恨」,讓我想起一段往事。那時我剛出版《孩子的我》,爸爸拖著病體南下參加我的新書分享會。在得知爸爸會出席時,我已準備好演講的簡報。簡報中摘錄書中的片段,我循著過往地景,談起童年中不堪的往事。我很猶豫是不是該從簡報中拿掉和爸爸有關的部分?後來還是留了下來。分享會尾聲,有讀者問爸爸,對於我所寫的有什麼想法?爸爸笑著回:「那都是事實啊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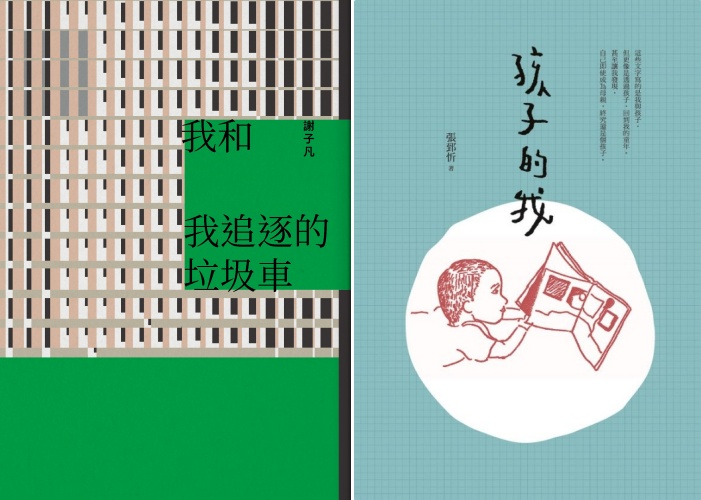
當爸爸說出那是事實時,我反而困惑了。我以文字寫下的真的是「真的」嗎?也許在某個角度來看確實如此,但並非事件的全貌。每當我要書寫親族,特別是以散文作為載體時,爸爸說那句話的聲音就會在我耳邊迴盪。相較之下,小說給予我更寬廣的探索空間。
還有,人的情緒總是太複雜,愛恨有時連自己都分辨不明。就我而言,實在很難完全將愛恨區別開來,不知道子凡對親族書寫的思索又是如何呢?
謝子凡:
突然想到呀,前美國第一夫人蜜雪兒在2018年出版自傳《成為這樣的我》,上了電視訪談,主持人中途請來歐巴馬加入談話。歐巴馬笑說,她說的與「事實」不完全相符;蜜雪兒(翻了白眼)笑笑反擊:「那是『我這方』的事實。」(That‘s MY version of reality.)
心理學上有種叫做「我訊息」的說法。就是溝通時先放下指著對方說「你怎樣怎樣」的「你訊息」,先說出「我」的感受,接著再表達我這樣感受的客觀事實,以及我希望未來可以怎麼處理的具體建言。「我訊息」傳達的也是一種「我這方的事實」。
我覺得,我們在文學裡處理的似乎也一直都是「我訊息」,必然也不停計算著與世界的摩擦力有幾何、自己能不能承擔等等。對我來說,盡量去指認當時的感情是什麼,似乎能幫助我在裡頭搖晃出一點空間。
所以說,這些接近都只是允許自己去想想看:咦,這是什麼?有可能是什麼黑暗的東西嗎?有可能是我沒想過的情緒嗎?對,我受傷了;對,我極度不爽;或是,對,那裡有愛。在恍然大悟的當下,也覺得身體深處有什麼地方鬆開了。
試圖接近那個不可言述的,我覺得很像郅忻在〈我也不想這樣〉一文寫到的情感,察覺了自己的隱隱不安,然後拉鋸,然後得到釋放(以及安古的拍拍)。
指認過後也並非不能推翻嘛,但沒有經過這層指認,我好像就到不了下一個地方。另一方面,在文字裡思考親族關係,雖然在精神層面或許獲得了許多東西,但是否反而忽略了實質相處的時光,這是我近日在默默反省的。
說起來,我與郅忻有許多相似的地方,同樣出身新竹,也是客家人。書中提到的客家歌謠〈阿揪箭〉讓我想起母親教我這首歌的情景;〈打粄歌〉、〈ㄤ咕仔〉則殘忍地使我想起油亮鮮豔的紅粄與香氣四溢的艾粄,還接連想起紅粄有綠豆餡、紅豆餡與花生粉餡的分別(真的好久沒想起來了)。回憶總是在我餓的時候補上一槍。
郅忻這本散文與小說《海市》是同時進行的對嗎?想請問郅忻是如何調配力氣完成這兩件事的呢?
➤愛可以不是零和遊戲
張郅忻:
謝謝子凡對「我訊息」的釋義,這說法讓我更坦然且自由許多。每次看子凡旁徵博引,就會想倘若可以真正聽子凡說話一定很精彩有趣吧。子凡提及的〈我也不想這樣〉一文,其實在刊登前,我也曾經歷一番掙扎。反而在真正刊登後,以及最後成書,透過印製的方正文字,一次次重新閱讀那一夜的我,才慢慢真正認識那樣的自己,甚至諒解自己。
對於在文字裡思索親族關係,而忽略實質相處一事,我記得在幾年前,曾有個朋友問我:「寫著寫著,會不會變成只能在文字裡愛人?」我被這句話切切實實的擊中,確實,我發現某些時候,我真的只能在文字裡愛人。又或許是,當時的我還不懂愛是什麼。但有了小孩後,他會不停向你索討一切的愛。擁抱、親吻,甚至直接了當的說:「媽媽愛弟弟!」在這些實質的相處中,我反而比較能理直氣壯地在可以寫作時就專心地寫。有時甚至是想短暫的逃避一下(笑)。只是對於阿婆,還有臨終的父親,確實會有一種虧欠,覺得自己可以陪伴的時間太少。
 《海市》寫作的時間比較早,已經完成初稿之後,接到了人間福報副刊的專欄邀請。所以是一邊寫專欄的短篇文字,一邊重新修改《海市》。大約從第二本書開始,我就開始一次處理兩種以上的題材,比如《我的肚腹裡有一片海洋》關於女性成為母親的思索,與《孩子的我》輯一中記錄孩子成長的部分,是在同一個時間創作的,只是思考的面向不同。
《海市》寫作的時間比較早,已經完成初稿之後,接到了人間福報副刊的專欄邀請。所以是一邊寫專欄的短篇文字,一邊重新修改《海市》。大約從第二本書開始,我就開始一次處理兩種以上的題材,比如《我的肚腹裡有一片海洋》關於女性成為母親的思索,與《孩子的我》輯一中記錄孩子成長的部分,是在同一個時間創作的,只是思考的面向不同。
這樣的節奏,讓我獲得轉換與喘氣的空間。其實在寫作《海市》的後期,我跟媽媽大吵一架,媽媽個性很硬,偏偏我又遺傳了她,母女冷戰很長一段時間。期間,我寫了〈飄洋過海來看你〉,回憶起曾經那樣一心想要找母親的自己。後來鼓起勇氣傳了一封簡訊給她,彼此才破了冰。
我很喜歡〈快感延遲〉這一篇,子凡透過吃東西、與愛人相見,以刻意放慢的速度,放大延遲快感來襲的那一刻。子凡總是能捕捉到這樣細微的情感流動與變化。我也注意到文章中寫到:「幼時從家裡坐公車到新竹市區,快的話,大約20分鐘即可到達;若坐到的是每站都停的普通號,則要將近30分鐘。」這個距離感跟我從湖口搭上電車到新竹市的時間差不多。因此,我總在子凡的文字中猜想著,子凡的家鄉究竟是哪裡呢?這讓我不禁想起讀竹女時來自各方的同學們。在文學創作的長程裡,我們也算是某種「同學」吧?願我們都能邁開步伐一步一步往前走,衷心期待子凡的下一本創作。
謝子凡:
郅忻提到孩子對愛的索討,因而「在這些實質的相處中,我反而比較能理直氣壯地在可以寫作時就專心地寫。」這段話讓我很有感觸。以往有時覺得愛是有限的,分給這個了,那個則必定要少去。愛可以不是零和遊戲,是可以再生的。可以給人,也可以給文學,可以給任何使你心動的事物。
郅忻「在同一段時間內,處理兩種以上的題材」,在其中能得到轉換與喘息的空間。原來兩種題材與文體的轉換可以帶來這樣的效果呀~我自己有時也會兩種文體交錯著寫,寫著寫著有些忐忑,懷疑是不是該先完成哪一邊。郅忻的分享讓我安心許多。
〈快感延遲〉裡寫的是竹東喔。在我3歲的時候,我們家從新竹市搬到竹東,15歲時又搬到新竹市。大學到了台北,至今在台北的時間也遠超過了新竹。在海外居住時,想念的「家鄉」是台北。但前陣子米其林公布必比登推薦名單,網友做了新竹的迷因圖,不是名單上一片空白,就是列名的全是麥當勞。
我~很~生~氣。會為它生氣的,應該就是很有感情的地方吧。
這次與郅忻的線上對談,雖然見不到人,但是也因而有了餘裕可以慢慢思索並回應,很珍惜每一次的往覆。
最後,謝謝郅忻在《憶曲心聲》中一篇篇的昨日重現。在〈旅行的意義〉中,郅忻寫道,幼時與阿公阿婆在假日早晨,「從家裡出發,沒有任何目的地,在鄉間小路上漫步」。這樣的晃盪實在叫人羨慕(熱騰騰的豆花也是),當中的隱喻似乎也呼之欲出:邁開步伐便是了。●
|
 憶曲心聲 憶曲心聲
作者:張郅忻
出版:九歌出版
定價:300元
【內容簡介➤】
|
|
作者簡介:張郅忻
1982年生於新竹。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、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。現專職寫作。希望透過書寫,尋找生命中往返流動的軌跡。著有散文集《我家是聯合國》、《我的肚腹裡有一片海洋》、《孩子的我》及長篇小說《織》、《海市》。曾於《蘋果日報》撰寫專欄「長大以後」,《人間福報.副刊》專欄「安咕安咕」、「憶曲心聲」。
獲選《文訊》21世紀上升星座散文類、入圍2018年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,並多次入選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,亦獲國立台灣文學館文學好書推廣推薦好書、九歌年度散文選。曾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長篇小說專案補助、文化部青年創作補助、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長篇歷史小說寫作計畫補助、桐花文學獎、客家歷史小說獎、九歌少兒文學獎等。
|
Tags:
謝子凡(左)、張郅忻
➤歌曲是因接觸世界而生的
謝子凡:
先謝謝郅忻,《憶曲心聲》讓我想起許多音樂帶來的美好時光,腦袋叮叮咚咚響個不停,像是按下琴鍵後,震動於空氣中的音符撞擊了各種物件,又分別綻放出自己的音色。
最近我正好在讀是枝裕和導演的書《我在拍電影時思考的事》,裡頭提到拍 攝歌手Cocco的紀錄片時,導演心裡的感受:「歌曲是因接觸世界而生的」。這句話用以形容《憶曲心聲》也是恰恰好的。郅忻的文字因歌曲而生,也收攏了當下的內心風景,是作者與世界的切面產生的真情互動。
攝歌手Cocco的紀錄片時,導演心裡的感受:「歌曲是因接觸世界而生的」。這句話用以形容《憶曲心聲》也是恰恰好的。郅忻的文字因歌曲而生,也收攏了當下的內心風景,是作者與世界的切面產生的真情互動。
我有一種感覺,郅忻的心像是精巧的玻璃風鈴,此書即是玲瓏心腸敲出的長長曲子。說是玻璃風鈴,是因為郅忻說起家人,無論是長輩或孩子,皆自然不保留,即使提起傷逝,情感亦透明可親。
要將對某首歌的深情化為篇章,實屬不易。歌曲有詞曲原本設定的意境,又需與自己所感做結合,想請郅忻分享一下這捕捉的手藝。是因為歌曲牽動了感情,進而召喚出場景;還是在此情此景之下,聽見了迴盪的背景音呢?
張郅忻:
謝謝子凡的閱讀與聆聽。聲音,確實是不可捉摸,卻又沒有什麼比它更能表達存在於內心深處、難以言喻的觸動與情緒。《憶曲心聲》原是我在人間福報副刊的專欄,最初是想記錄兒時聽過的客家歌曲與念謠,那時父喪不久,總覺得四方歌聲都有父親的影子。我才醒悟,儘管曾有怨懟,我依舊還是那個依賴父親的小女孩。於是,專欄也開始寫了與父親回憶有關的歌。如父親臨終時我才知曉的〈給你呆呆〉,還有父親拿起麥克風必唱的張雨生〈大海〉。關於子凡的提問,似乎是兩者都有。有時是點播記憶中的歌,進而召喚情感。有時則是忽然在某個時刻,耳邊響起舊時的樂音。
我們在聆聽一首歌時,總是會想起某一個人或第一次聽見這首歌的場景。這使我們經常「誤讀」一首歌,然後在漫漫的成長之途中重新認識它。比如子凡在〈與你的相對位置〉中,提到哥哥在上舖哼著羅大佑的〈亞細亞的孤兒〉。年紀尚小的我,是聽小叔叔播放的,懵懂間跟著哼唱「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」,只是當時怎會知道那玩具竟如此沉重?但,這種「誤讀」讓一首歌對不同聆聽者有了殊異體驗。不知道子凡如何看待這種「誤讀」或「誤聽」?
➤誤讀之外,讀者的江湖道義
謝子凡:
誤讀經常發生,甚至是必然的。
如我輩聽團仔必聽的1976,每每唱起名曲之一〈方向感〉的時候,全場都會跟著嘶吼:「也許你該學習相信自己的方向感」,現場幾成暴動狀態。我相信這時大家心中想的,是在徬徨中想抓住些什麼的自己。
但主唱阿凱曾半開玩笑地說這原本是一首渣男之歌,本意是在感情中,「我」不想擔負指南針的角色,你去尋找自己的方向感吧。
有名的誤讀還有工人皇帝Bruce Springsteen,一首激昂的〈Born in the USA〉曾被美國政治人物選為競選歌曲。然而歌詞所述的是藉由一名越戰退伍軍人之口,控訴這塊土地的種種不公,Demo帶的初版編曲更是幽幽怨怨如泣如訴。後來發行時採取與歌詞相反的音樂意象,頗有反諷意味。所以當有人眼神閃亮地唱著這首歌時,我都覺得饒富趣味。
我又接著想到,是枝裕和帶著《幻之光》參加法國的南特三洲影展時,觀眾在映後座談會上熱烈討論「究竟從哪裡開始是夢境?」,當導演想要開口時,還被觀眾制止,「導演請先別說」,而觀眾繼續各自訴說自己的看法。
總之誤讀看來不可避免。而抽離出來看他人的各種誤讀,再對照作者原意,也成另一種有意思的風景。
但作為一個讀者、聽眾,在相信自己的感受之餘,同時努力去靠近作者,也是身為讀者的江湖道義(笑),我是這麼覺得的。郅忻的看法又是怎麼樣的呢?
郅忻在這本書裡採取了非常溫柔的切入點,接下來這個問題是我自己近期的思索,剛好有這難得的機會,便大膽提問:在親族的感情上,有沒有可能——可以恨,所以其他部分才可以愛?許多感情就是糾結在又愛又恨,所以處理不來。想要愛他,但又有地方是絕對不想原諒的。想要恨他,一些自己相信是愛的記憶卻也揮之不去。我們在處理生命難題時,有沒有可能切割開來,分開談愛與恨(或是愛與不愛)?
➤指認,然後到下一個地方
張郅忻:
謝謝子凡分享如此精彩的誤讀經驗。我一邊聽著這些歌曲,一邊重新咀嚼子凡的文字。當我放大了耳朵,才聽見〈我和我追逐的垃圾車〉中多層次的聲音。那些圍繞生活的聲響,如租屋處隔壁吃著鹹酥雞的聲音、辦公室裡細碎交談聲,最終以垃圾車播放的「少女的祈禱」作為結束。我彷彿走進一個精心佈置的聲響世界,在字裡行間尋覓作者的身影。
對於子凡詢問在書寫中如何處理關於親族的「愛」與「恨」,讓我想起一段往事。那時我剛出版《孩子的我》,爸爸拖著病體南下參加我的新書分享會。在得知爸爸會出席時,我已準備好演講的簡報。簡報中摘錄書中的片段,我循著過往地景,談起童年中不堪的往事。我很猶豫是不是該從簡報中拿掉和爸爸有關的部分?後來還是留了下來。分享會尾聲,有讀者問爸爸,對於我所寫的有什麼想法?爸爸笑著回:「那都是事實啊。」
當爸爸說出那是事實時,我反而困惑了。我以文字寫下的真的是「真的」嗎?也許在某個角度來看確實如此,但並非事件的全貌。每當我要書寫親族,特別是以散文作為載體時,爸爸說那句話的聲音就會在我耳邊迴盪。相較之下,小說給予我更寬廣的探索空間。
還有,人的情緒總是太複雜,愛恨有時連自己都分辨不明。就我而言,實在很難完全將愛恨區別開來,不知道子凡對親族書寫的思索又是如何呢?
謝子凡:
突然想到呀,前美國第一夫人蜜雪兒在2018年出版自傳《成為這樣的我》,上了電視訪談,主持人中途請來歐巴馬加入談話。歐巴馬笑說,她說的與「事實」不完全相符;蜜雪兒(翻了白眼)笑笑反擊:「那是『我這方』的事實。」(That‘s MY version of reality.)
心理學上有種叫做「我訊息」的說法。就是溝通時先放下指著對方說「你怎樣怎樣」的「你訊息」,先說出「我」的感受,接著再表達我這樣感受的客觀事實,以及我希望未來可以怎麼處理的具體建言。「我訊息」傳達的也是一種「我這方的事實」。
我覺得,我們在文學裡處理的似乎也一直都是「我訊息」,必然也不停計算著與世界的摩擦力有幾何、自己能不能承擔等等。對我來說,盡量去指認當時的感情是什麼,似乎能幫助我在裡頭搖晃出一點空間。
所以說,這些接近都只是允許自己去想想看:咦,這是什麼?有可能是什麼黑暗的東西嗎?有可能是我沒想過的情緒嗎?對,我受傷了;對,我極度不爽;或是,對,那裡有愛。在恍然大悟的當下,也覺得身體深處有什麼地方鬆開了。
試圖接近那個不可言述的,我覺得很像郅忻在〈我也不想這樣〉一文寫到的情感,察覺了自己的隱隱不安,然後拉鋸,然後得到釋放(以及安古的拍拍)。
指認過後也並非不能推翻嘛,但沒有經過這層指認,我好像就到不了下一個地方。另一方面,在文字裡思考親族關係,雖然在精神層面或許獲得了許多東西,但是否反而忽略了實質相處的時光,這是我近日在默默反省的。
說起來,我與郅忻有許多相似的地方,同樣出身新竹,也是客家人。書中提到的客家歌謠〈阿揪箭〉讓我想起母親教我這首歌的情景;〈打粄歌〉、〈ㄤ咕仔〉則殘忍地使我想起油亮鮮豔的紅粄與香氣四溢的艾粄,還接連想起紅粄有綠豆餡、紅豆餡與花生粉餡的分別(真的好久沒想起來了)。回憶總是在我餓的時候補上一槍。
郅忻這本散文與小說《海市》是同時進行的對嗎?想請問郅忻是如何調配力氣完成這兩件事的呢?
➤愛可以不是零和遊戲
張郅忻:
謝謝子凡對「我訊息」的釋義,這說法讓我更坦然且自由許多。每次看子凡旁徵博引,就會想倘若可以真正聽子凡說話一定很精彩有趣吧。子凡提及的〈我也不想這樣〉一文,其實在刊登前,我也曾經歷一番掙扎。反而在真正刊登後,以及最後成書,透過印製的方正文字,一次次重新閱讀那一夜的我,才慢慢真正認識那樣的自己,甚至諒解自己。
對於在文字裡思索親族關係,而忽略實質相處一事,我記得在幾年前,曾有個朋友問我:「寫著寫著,會不會變成只能在文字裡愛人?」我被這句話切切實實的擊中,確實,我發現某些時候,我真的只能在文字裡愛人。又或許是,當時的我還不懂愛是什麼。但有了小孩後,他會不停向你索討一切的愛。擁抱、親吻,甚至直接了當的說:「媽媽愛弟弟!」在這些實質的相處中,我反而比較能理直氣壯地在可以寫作時就專心地寫。有時甚至是想短暫的逃避一下(笑)。只是對於阿婆,還有臨終的父親,確實會有一種虧欠,覺得自己可以陪伴的時間太少。
這樣的節奏,讓我獲得轉換與喘氣的空間。其實在寫作《海市》的後期,我跟媽媽大吵一架,媽媽個性很硬,偏偏我又遺傳了她,母女冷戰很長一段時間。期間,我寫了〈飄洋過海來看你〉,回憶起曾經那樣一心想要找母親的自己。後來鼓起勇氣傳了一封簡訊給她,彼此才破了冰。
我很喜歡〈快感延遲〉這一篇,子凡透過吃東西、與愛人相見,以刻意放慢的速度,放大延遲快感來襲的那一刻。子凡總是能捕捉到這樣細微的情感流動與變化。我也注意到文章中寫到:「幼時從家裡坐公車到新竹市區,快的話,大約20分鐘即可到達;若坐到的是每站都停的普通號,則要將近30分鐘。」這個距離感跟我從湖口搭上電車到新竹市的時間差不多。因此,我總在子凡的文字中猜想著,子凡的家鄉究竟是哪裡呢?這讓我不禁想起讀竹女時來自各方的同學們。在文學創作的長程裡,我們也算是某種「同學」吧?願我們都能邁開步伐一步一步往前走,衷心期待子凡的下一本創作。
謝子凡:
郅忻提到孩子對愛的索討,因而「在這些實質的相處中,我反而比較能理直氣壯地在可以寫作時就專心地寫。」這段話讓我很有感觸。以往有時覺得愛是有限的,分給這個了,那個則必定要少去。愛可以不是零和遊戲,是可以再生的。可以給人,也可以給文學,可以給任何使你心動的事物。
郅忻「在同一段時間內,處理兩種以上的題材」,在其中能得到轉換與喘息的空間。原來兩種題材與文體的轉換可以帶來這樣的效果呀~我自己有時也會兩種文體交錯著寫,寫著寫著有些忐忑,懷疑是不是該先完成哪一邊。郅忻的分享讓我安心許多。
〈快感延遲〉裡寫的是竹東喔。在我3歲的時候,我們家從新竹市搬到竹東,15歲時又搬到新竹市。大學到了台北,至今在台北的時間也遠超過了新竹。在海外居住時,想念的「家鄉」是台北。但前陣子米其林公布必比登推薦名單,網友做了新竹的迷因圖,不是名單上一片空白,就是列名的全是麥當勞。
我~很~生~氣。會為它生氣的,應該就是很有感情的地方吧。
這次與郅忻的線上對談,雖然見不到人,但是也因而有了餘裕可以慢慢思索並回應,很珍惜每一次的往覆。
最後,謝謝郅忻在《憶曲心聲》中一篇篇的昨日重現。在〈旅行的意義〉中,郅忻寫道,幼時與阿公阿婆在假日早晨,「從家裡出發,沒有任何目的地,在鄉間小路上漫步」。這樣的晃盪實在叫人羨慕(熱騰騰的豆花也是),當中的隱喻似乎也呼之欲出:邁開步伐便是了。●
作者:張郅忻
出版:九歌出版
定價:300元
【內容簡介➤】
作者簡介:張郅忻
1982年生於新竹。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、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。現專職寫作。希望透過書寫,尋找生命中往返流動的軌跡。著有散文集《我家是聯合國》、《我的肚腹裡有一片海洋》、《孩子的我》及長篇小說《織》、《海市》。曾於《蘋果日報》撰寫專欄「長大以後」,《人間福報.副刊》專欄「安咕安咕」、「憶曲心聲」。
獲選《文訊》21世紀上升星座散文類、入圍2018年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,並多次入選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,亦獲國立台灣文學館文學好書推廣推薦好書、九歌年度散文選。曾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長篇小說專案補助、文化部青年創作補助、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長篇歷史小說寫作計畫補助、桐花文學獎、客家歷史小說獎、九歌少兒文學獎等。
手指點一下,您支持的每一分錢
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
閱讀通信 vol.369》出烤箱的好日子
延伸閱讀
對談》鄉野和民俗裡的溫柔:張嘉祥、謝宜安談《夜官巡場》
裝咖人樂團主唱張嘉祥以成長的嘉義火燒庄(現民雄地區)為藍本,用音樂和文字起造一座魔幻的民雄地方誌,出版《夜官巡場》小說及同名專輯,將故鄉的正史野史、... 閱讀更多
對談》喜歡,讓你在對的狀態,做出好玩不過時的東西:唱作漫畫家奇哥╳音樂人馬念先
閱讀更多
現場》「參詳.當代客家文藝沙龍」:客籍文學家的私房文學走讀路線大公開
匯聚各界文學、藝術、文史、飲食、語言、地方創生等領域文化人,共同商討交流當代文化藝術與客家議題的「參詳camˊ xiongˇ.當代客家文藝沙龍」,... 閱讀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