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同志文學」已是台灣文學研究公認存在且一再討論的類別,但是,如果作者本人不是已出櫃的現身同志(例如陳克華),作品中沒有昭然揭開的同志主體(例如《孽子》)——即「看得見的同志」——則讀者與論者不能分辨,或雖然臆想、耳語,卻不敢率爾歸入此一標籤底下。
紀大偉《同志文學史:台灣的發明》雖然在書名就用上了「同志文學」一詞,但從〈緒論〉裡就已經不憚其煩地說明,他的立論正是要從質疑這個詞開始。
再者,「台灣的發明」也可能讓讀者驚詫:「同性戀」不是「舶來品」嗎?歐美這些「先進」地方不是比台灣更早就出現「同志文學」嗎?同樣的,紀大偉也在〈緒論〉裡一而再地解說他的理論資源與觀點啟迪:一是黑普林(David Halperin)指出的,同志的歷史不是從歷史中被挖掘出來,而是一代代讀者與評論者「以後見之明所『發明』並『補綴』而成」;二是霍布斯邦(Eric Hobsbawn)提出的,許多「悠久傳統」其實是現代化進程中的發明物,那些「慣例」並非天成。因此,這裡的「發明」並非指器物的創造,而是觀念上的除魅。
將「性」理解為參與成員複雜的「機制」,而不只是「性行為」的收納盒。
除了挑明其解構立場,紀大偉也強調,這部書乃是站在「公眾歷史」的角度,由下而上發揮力量,以在野抵抗主流歷史的壓力。「公眾歷史」一般以民眾口述史的方式呈現,但是在台灣戒嚴時代,願意提供口述史的同志很少,「想要認識戒嚴時期台灣同志人口的國內外研究者,經常採取同志口述歷史的『替代品』:同志文學。」因此,本書並不單單聚焦在大師、名作,而是定位在「以文學為基地的『文化史』」。不「純」的文學、非文學也要納進來,才能拼組出多元複雜面貌。
進一步看,紀大偉想提出比「同志文學」這個「文類」(genre)再擴大些的,「同志文學」這個「領域」(field)。那些議論同志、抹黑同志、誤解同志等的報章碎片與評說文章,雖納不入「文類」,卻絕對是屬於此一「領域」,值得一同檢視。
「駁雜」正是社會的實況,性別領域也是一樣,故本書中正視的不僅僅是材料的「駁雜」,也包含小說內呈現出來的性相上的「駁雜」。不是只有異性戀、同性戀之分,同一個角色也未必得固著在一種身分上,甚至不同性取向之間,也可能必須合作才能生存。以紀大偉自己的話來說,就是「將『性』理解為參與成員複雜的『機制』,而不只是『性行為』的收納盒。」
過往研究者以尋找「看得見的同志」來判定此一作品是否為「同志文學」,紀大偉卻提出,「同志文學」重要的不只「同志」,還有「文學」。「文學」裡的主體時常是「假、虛、無」,不是那麼輕鬆確切立刻可以捕捉、不費力氣的。然而,假作真時真亦假,「假、虛、無」的曖昧、勾引,使讀者於影影綽綽中感受到同性戀,暗香浮動,卻入木三分。這種文學表現,是注重讀者甚於作者,既有文學本身的需求,也與作品生產的社會環境有關。
也許有些讀者會急著想看看紀大偉羅列了哪些同志文學清單、怎樣解讀那些著名的同志文學作品,但是,《同志文學史》緒論這一章絕不可放過。我認為,若是沒有先將這部書緒論裡種種思辨過程先過一遍,就不能適切理解之後他對於文本的實際分析。
緒論裡提示的理論資源、對西方學術論述的取捨與反駁,對於我們思考同志文學,甚至是思考所有弱勢文學,均極有幫助。同時,書中也扼要地說明了「同性戀」、「同志」、「酷兒」的立場與關懷面向的差異,並指出這些詞彙在翻譯旅行上,也會因為應對話題、語境而出現參差,並非均質的存在。
《孽子》沒讓讀者看到贏家,顧肇森的〈張偉〉等篇章,同性戀主角都是社會上的成功人士——所以,假如顧肇森寫了比較弱勢的同性戀者,是不是他在文學上的道德位置就會比較受肯定呢?
有趣的是,長年累積修改而成的《同志文學史》,在此出版時刻,恰恰應對了過去半年在青年讀者之間討論火熱的兩位重要小說家,一是逝世不久、通常是在國族議題上造成爭端的陳映真,二是在臉書上發表反同言論而遭圍剿的宋澤萊。陳映真〈趙南棟〉與〈纍纍〉裡,滿布著男性著迷於觀看男性的視線;宋澤萊早年作品《紅樓舊事》的小說主人翁,則同時探索人生哲學與(包含同性)情慾。而與〈纍纍〉同樣表現軍營內男男情慾文化的,還包括在不同著作中一再處理類似軍中題材的履彊。這幾位作者,恐怕都不是過去開列「同志文學」書目時會出現的小說家。這也是紀大偉立定於「領域」和「假、虛、無」主體上,將文本裡的叢結一一梳開的貢獻。
不過,相較於對以上三者小說的細膩判讀(尤其是針對陳映真〈趙南棟〉,特別過癮),我以為紀大偉對老早就被納入「同志文學『文類』」的顧肇森小說太過嚴厲。書中指出,主角太過傲人而順遂的學業與工作生涯,傳遞「同性戀不僅和大家都一樣,而且比一般人還傑出」,延伸來說是社會應該接納同性戀者,不僅因為他們和一般人沒什麼差別,還更有消費力。因此,紀大偉認為這篇作品未曾關注到同性戀與其他社會邊緣人的處境,反而頌揚了個人造化上的僥倖。相較來說,《孽子》沒讓讀者看到贏家,而顧肇森的〈張偉〉等篇章,同性戀主角都是社會上的成功人士——所以,假如顧肇森寫了比較弱勢的同性戀者,是不是他在文學上的道德位置就會比較受肯定呢?
其實總括「旅美華人譜」系列,人物階層光譜是很廣的。我認為與其責備顧肇森不顧及同性戀裡的社會邊緣人,不如說,他描繪的中產階級同性戀,和白先勇筆下的新公園男妓,一起拚組出同志文學的不同夾層。
〈張偉〉主角造訪新公園後,覺得裡頭都是些「孤魂孽鬼」,他不敢想像自己竟會屬於這個世界——「那麼他屬於什麼世界?原來他屬於美國。」紀大偉挪用自吉見俊哉而提出的「內在(台灣境內的美國文化)/外在美國(台灣境外的美國領土)」,在同志文學裡,這種朝美國匍匐而去的傾向,是與俗語「美國時間」指稱的從日常主流時間中逃逸的狀態結合,作品中的台灣人往往是在美國看到同性戀,或是台灣人在美國獲致了不同尋常的情欲經驗,或者是於台灣境內傳遞美國風味的咖啡室、戲院等地,得到同性戀知識或見識同性戀情慾等等。在這些「內/外在美國」裡得到的「美國時間」,正是叛離普通人時間表,從中騰挪、開啟的。紀大偉也注意到了性別差異,女同志文本中反而是盤算如何就近與女人相聚,而非寄託於遠方。
以「愛滋」取代「解嚴」來討論同志文學的轉變,希望能甩脫過去文學史敘述過度依附於政治大歷史的習慣。再者,也指出印刷文化如何形構出論說、接受同性戀的環境,將之視為同志文學現身的前導。
本書以小說討論為主軸,對於散文和新詩較未深入。不過,新詩部分引用鯨向海的觀察與主張,與紀大偉若干主張不謀而合。全書論述結構則於1960年代以降,以10年為單位,看起來似乎與一般文學史無異。不過,1970年代區分為女女與男男各一章,之間仍有細膩的區分,在女女一章強調不同性向合作下的經濟實踐,在男男一章強調「美國時間」的空間化。1980年代以降至世紀末,則不再區分男女,而是呈現「罷家」以後才能「成人」的不同樣態,並以「愛滋」取代「解嚴」來討論同志文學的轉變,希望能甩脫過去文學史敘述過度依附於政治大歷史的習慣。再者,也指出印刷文化如何形構出論說、接受同性戀的環境,將之視為同志文學現身的前導。書中雖然極力打破過去將白先勇《孽子》視為台灣同志文學源頭的說法,卻也還是將之視為「讓國內外讀者駐足討論台灣文學/同志文學/同性戀」的公共平台,強調無數讀者一同創造出這部小說在同志言說範圍裡的厚度。
最後,《同志文學史》提供了一份「廣義的同志文學領域參與者」書單,範圍甚至及於極為年輕的林佑軒(1987—)。我願意盡棉薄之力,再補充兩本無論在「文類」或「領域」都應該納入的著作:一是騷夏詩集《瀕危動物》,她以「我身上所有開孔的地方都非常害怕妳,但也非常思念妳」這樣的詩句震動讀者,二是聲稱「我從來不在櫃子裡啊」的景翔的詩集《長夜之旅》。●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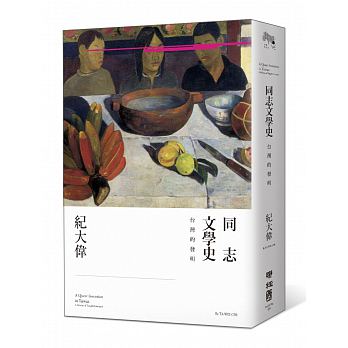
同志文學史:台灣的發明
作者:紀大偉
出版:聯經出版公司
定價:650元
【內容簡介 】 】

紀大偉:
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,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(UCLA)比較文學博士。著有學術專書《同志文學史》、小說集《膜》(已有日文翻譯版、法文翻譯版)等,雜文集《晚安巴比倫》等。 |
Tags:
「同志文學」已是台灣文學研究公認存在且一再討論的類別,但是,如果作者本人不是已出櫃的現身同志(例如陳克華),作品中沒有昭然揭開的同志主體(例如《孽子》)——即「看得見的同志」——則讀者與論者不能分辨,或雖然臆想、耳語,卻不敢率爾歸入此一標籤底下。
紀大偉《同志文學史:台灣的發明》雖然在書名就用上了「同志文學」一詞,但從〈緒論〉裡就已經不憚其煩地說明,他的立論正是要從質疑這個詞開始。
再者,「台灣的發明」也可能讓讀者驚詫:「同性戀」不是「舶來品」嗎?歐美這些「先進」地方不是比台灣更早就出現「同志文學」嗎?同樣的,紀大偉也在〈緒論〉裡一而再地解說他的理論資源與觀點啟迪:一是黑普林(David Halperin)指出的,同志的歷史不是從歷史中被挖掘出來,而是一代代讀者與評論者「以後見之明所『發明』並『補綴』而成」;二是霍布斯邦(Eric Hobsbawn)提出的,許多「悠久傳統」其實是現代化進程中的發明物,那些「慣例」並非天成。因此,這裡的「發明」並非指器物的創造,而是觀念上的除魅。
除了挑明其解構立場,紀大偉也強調,這部書乃是站在「公眾歷史」的角度,由下而上發揮力量,以在野抵抗主流歷史的壓力。「公眾歷史」一般以民眾口述史的方式呈現,但是在台灣戒嚴時代,願意提供口述史的同志很少,「想要認識戒嚴時期台灣同志人口的國內外研究者,經常採取同志口述歷史的『替代品』:同志文學。」因此,本書並不單單聚焦在大師、名作,而是定位在「以文學為基地的『文化史』」。不「純」的文學、非文學也要納進來,才能拼組出多元複雜面貌。
進一步看,紀大偉想提出比「同志文學」這個「文類」(genre)再擴大些的,「同志文學」這個「領域」(field)。那些議論同志、抹黑同志、誤解同志等的報章碎片與評說文章,雖納不入「文類」,卻絕對是屬於此一「領域」,值得一同檢視。
「駁雜」正是社會的實況,性別領域也是一樣,故本書中正視的不僅僅是材料的「駁雜」,也包含小說內呈現出來的性相上的「駁雜」。不是只有異性戀、同性戀之分,同一個角色也未必得固著在一種身分上,甚至不同性取向之間,也可能必須合作才能生存。以紀大偉自己的話來說,就是「將『性』理解為參與成員複雜的『機制』,而不只是『性行為』的收納盒。」
過往研究者以尋找「看得見的同志」來判定此一作品是否為「同志文學」,紀大偉卻提出,「同志文學」重要的不只「同志」,還有「文學」。「文學」裡的主體時常是「假、虛、無」,不是那麼輕鬆確切立刻可以捕捉、不費力氣的。然而,假作真時真亦假,「假、虛、無」的曖昧、勾引,使讀者於影影綽綽中感受到同性戀,暗香浮動,卻入木三分。這種文學表現,是注重讀者甚於作者,既有文學本身的需求,也與作品生產的社會環境有關。
也許有些讀者會急著想看看紀大偉羅列了哪些同志文學清單、怎樣解讀那些著名的同志文學作品,但是,《同志文學史》緒論這一章絕不可放過。我認為,若是沒有先將這部書緒論裡種種思辨過程先過一遍,就不能適切理解之後他對於文本的實際分析。
緒論裡提示的理論資源、對西方學術論述的取捨與反駁,對於我們思考同志文學,甚至是思考所有弱勢文學,均極有幫助。同時,書中也扼要地說明了「同性戀」、「同志」、「酷兒」的立場與關懷面向的差異,並指出這些詞彙在翻譯旅行上,也會因為應對話題、語境而出現參差,並非均質的存在。
有趣的是,長年累積修改而成的《同志文學史》,在此出版時刻,恰恰應對了過去半年在青年讀者之間討論火熱的兩位重要小說家,一是逝世不久、通常是在國族議題上造成爭端的陳映真,二是在臉書上發表反同言論而遭圍剿的宋澤萊。陳映真〈趙南棟〉與〈纍纍〉裡,滿布著男性著迷於觀看男性的視線;宋澤萊早年作品《紅樓舊事》的小說主人翁,則同時探索人生哲學與(包含同性)情慾。而與〈纍纍〉同樣表現軍營內男男情慾文化的,還包括在不同著作中一再處理類似軍中題材的履彊。這幾位作者,恐怕都不是過去開列「同志文學」書目時會出現的小說家。這也是紀大偉立定於「領域」和「假、虛、無」主體上,將文本裡的叢結一一梳開的貢獻。
不過,相較於對以上三者小說的細膩判讀(尤其是針對陳映真〈趙南棟〉,特別過癮),我以為紀大偉對老早就被納入「同志文學『文類』」的顧肇森小說太過嚴厲。書中指出,主角太過傲人而順遂的學業與工作生涯,傳遞「同性戀不僅和大家都一樣,而且比一般人還傑出」,延伸來說是社會應該接納同性戀者,不僅因為他們和一般人沒什麼差別,還更有消費力。因此,紀大偉認為這篇作品未曾關注到同性戀與其他社會邊緣人的處境,反而頌揚了個人造化上的僥倖。相較來說,《孽子》沒讓讀者看到贏家,而顧肇森的〈張偉〉等篇章,同性戀主角都是社會上的成功人士——所以,假如顧肇森寫了比較弱勢的同性戀者,是不是他在文學上的道德位置就會比較受肯定呢?
其實總括「旅美華人譜」系列,人物階層光譜是很廣的。我認為與其責備顧肇森不顧及同性戀裡的社會邊緣人,不如說,他描繪的中產階級同性戀,和白先勇筆下的新公園男妓,一起拚組出同志文學的不同夾層。
〈張偉〉主角造訪新公園後,覺得裡頭都是些「孤魂孽鬼」,他不敢想像自己竟會屬於這個世界——「那麼他屬於什麼世界?原來他屬於美國。」紀大偉挪用自吉見俊哉而提出的「內在(台灣境內的美國文化)/外在美國(台灣境外的美國領土)」,在同志文學裡,這種朝美國匍匐而去的傾向,是與俗語「美國時間」指稱的從日常主流時間中逃逸的狀態結合,作品中的台灣人往往是在美國看到同性戀,或是台灣人在美國獲致了不同尋常的情欲經驗,或者是於台灣境內傳遞美國風味的咖啡室、戲院等地,得到同性戀知識或見識同性戀情慾等等。在這些「內/外在美國」裡得到的「美國時間」,正是叛離普通人時間表,從中騰挪、開啟的。紀大偉也注意到了性別差異,女同志文本中反而是盤算如何就近與女人相聚,而非寄託於遠方。
本書以小說討論為主軸,對於散文和新詩較未深入。不過,新詩部分引用鯨向海的觀察與主張,與紀大偉若干主張不謀而合。全書論述結構則於1960年代以降,以10年為單位,看起來似乎與一般文學史無異。不過,1970年代區分為女女與男男各一章,之間仍有細膩的區分,在女女一章強調不同性向合作下的經濟實踐,在男男一章強調「美國時間」的空間化。1980年代以降至世紀末,則不再區分男女,而是呈現「罷家」以後才能「成人」的不同樣態,並以「愛滋」取代「解嚴」來討論同志文學的轉變,希望能甩脫過去文學史敘述過度依附於政治大歷史的習慣。再者,也指出印刷文化如何形構出論說、接受同性戀的環境,將之視為同志文學現身的前導。書中雖然極力打破過去將白先勇《孽子》視為台灣同志文學源頭的說法,卻也還是將之視為「讓國內外讀者駐足討論台灣文學/同志文學/同性戀」的公共平台,強調無數讀者一同創造出這部小說在同志言說範圍裡的厚度。
最後,《同志文學史》提供了一份「廣義的同志文學領域參與者」書單,範圍甚至及於極為年輕的林佑軒(1987—)。我願意盡棉薄之力,再補充兩本無論在「文類」或「領域」都應該納入的著作:一是騷夏詩集《瀕危動物》,她以「我身上所有開孔的地方都非常害怕妳,但也非常思念妳」這樣的詩句震動讀者,二是聲稱「我從來不在櫃子裡啊」的景翔的詩集《長夜之旅》。●
同志文學史:台灣的發明 】
】
作者:紀大偉
出版:聯經出版公司
定價:650元
【內容簡介
紀大偉:
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,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(UCLA)比較文學博士。著有學術專書《同志文學史》、小說集《膜》(已有日文翻譯版、法文翻譯版)等,雜文集《晚安巴比倫》等。
手指點一下,您支持的每一分錢
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
閱讀通信 vol.366》為什麼要叫勇者,不叫英雄?